1990年3月某日我到了中正紀念堂,因為有一位我欣賞愛慕的同學已經在這裡拍攝影像紀錄多日。當年的我,也懷抱著一種用影像記錄大時代故事的理想,帶著我的二手CANON,翹課要來拍攝學生抗議萬年老國代選總統的運動。
事件的發展很急速,我們成為歷史的見證者,本來是要來記錄歷史,而自己也捲入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但每個人所看的歷史又是不同的視角,就像我當時的相機,我是用我的視窗在見識這個世界發生的事物,本來是這個事件外的觀察者,但依我雞婆的個性,難免放下相機,成為事件轉折的一個齒輪。
應該是3月19日吧!到達廣場的第一天晚上淒風苦雨,有十幾個學生坐在大中至正牌樓的圍牆邊靜坐抗議,有支持的守護者,也有看熱鬧的民眾,還有掛著各種抗爭訴求的民眾。現場傳言晚上會被掃平清場,雖然已經解嚴了,但不知這幾個年輕的頭顱,是會被坦克輾過?還是會被蓋布袋,丟到海裡?他們抱持著從容赴義的精神,等待中有種緊張肅殺的氣氛,一有風吹草動或一點聲響,不同黨派意見者的爭執聲稍微嚷嚷,都會帶來一陣不安和騷動。我看到一位東海的學長名叫方孝鼎發起絕食抗議,他和幾位響應者一同坐在大中至正的牌樓下和原本的靜坐者不同位置,被媒體和熱心群眾包圍,當然也有謾罵者叫囂。我正覺得奇怪,打聽之下才知,有新加入的學生提議,要拉高抗爭態勢才能激起媒體注意,但原發起學生的組織討論後決議,不走激烈抗爭路線,保持和平理性,否決了這項提議。所以提議絕食抗爭的一小群人另外在旁邊發起絕食抗爭,這時候學生意見分為兩派,感覺上好像還沒開始產生力量就分裂了,但事情的發展往往在意料之外,因為這位學長的發言非常令人感動,立刻就有媒體說他是「台版吾爾開希」之類的比喻(其實他很不喜歡這個比喻),透過當時才剛開放不久的各家媒體大放送,學生人潮從四面八方湧入,連北一女、成功、建中等中學生也都自動罷課紛紛舉起紙板加入……。
一下子人數多到牌樓已經擠不下,學生順勢搬進去廣場,「佔領」了演藝廳騎樓,迅速成立指揮部。不久之後,圍起封鎖線,把「單純的學生」和「複雜的社會民眾」隔出一條線,封鎖線裡的自治區是學生實施民主自治的實驗農場。沒有多久重新改組學生議會,樓梯放下一塊放長長的大字,寫著「自由之愛」。這條封鎖線曾經被有心人刻意批評,但我覺得這真是當時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最偉大的發明!封鎖線外不斷傳進來睡袋、食物等物資。總之,民眾不斷在線外加油,也有人在叫囂對罵,也有著急的家長在找子女。糾察隊外圍還有一層志工,自動組織保護學生(因為天安門事件才剛發生不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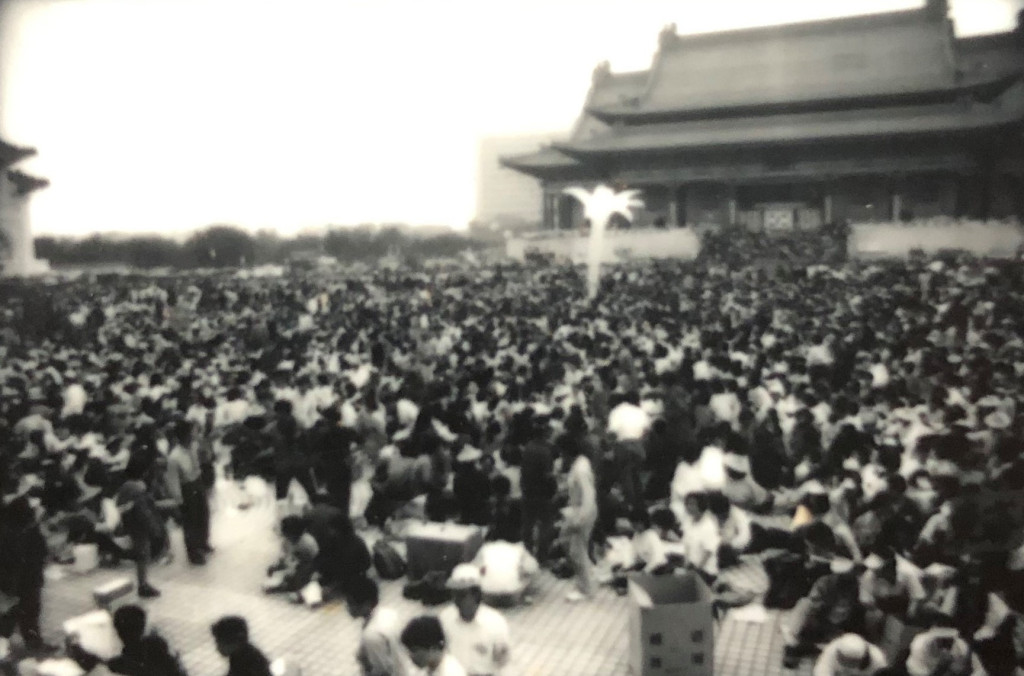
1990年3月學運,作者所記錄的現場照片。圖/鄧淑慧攝影提供
我本來只想翹課一天,眼看著局勢發展直覺這將是台灣歷史中的大事,不得不留在現場以免錯過這麼重要的歷史事件!沒想到一不小心也成為這場學運「野百合」精神象徵的發想者。對於自己無意中成為社會事件的一環,回想起來到底還是性格裡有一種俠義精神吧!雖然懵懂無知憑感覺做事,但卻是一個方向感正確的人!

1990年3月學運一景。圖/鄧淑慧攝影提供
我在跑來跑去拍照的過程,想像著將來自己會變成這一頁史詩的導演,在現場的那一刻,我已經在構思五十年後拍攝電影場景的畫面,雖然當年還沒有空拍機,但我已經看到高空環景拍攝的畫面將會是多麼動人!當時底片還很貴,窮學生的我絕不能輕易亂按快門,每一個畫面的取景得都是用盡全身的敏感度去取鏡!有時我也會捕捉一下那位令我心儀景仰的學長,感覺上他才是這個大時代影像紀錄片工作者的權威,我只是個剛學會攝影的影像狂熱分子,為了抓住剎那的瞬間而自我感動,當時的我也還抱著希望,我所捕捉到的畫面將來能提供後人製作紀錄片,成為感人的黑白照。

媒體採訪野百合運動時的動態。示意圖/鄧淑慧攝影提供
忘記第幾天了,應該是進入廣場的當天吧,指揮中心傳來廣播:「各校如有美術相關科系,請派一名到指揮中心左邊開會!」。因為有人提議這場學生運動要有一個精神象徵!放眼望去東海美術系還沒有人來,因為我剛從美術系轉社會系,所以我知道的美術系同學,除了那位真正在拍攝紀錄片的同學,還沒人來,社會系的同學就說,那你就代表東海去吧!開會的「代表」大概十幾人,印象中有台大、文化、實踐……。其中就原提議者要做一個「鍾馗」作為精神堡壘,指揮中心為了展現民主精神特別獨立召開這個會議,為了慎重請各校派代表參加。當時我一聽到精神象徵要用「鍾馗」就直覺太老掉牙了,就提議應該用清新一點,例如3月開的花吧!一時之間也還想不起來3月有什麼花?我請大家發想一下,有人說台北市花—杜鵑、有人說百合。一聽到百合,我就說:「啊!可以用台灣野百合,我在蘭嶼有看到滿山遍野,聽說是台灣的原生種,以前郊外很多遍佈全台灣」。講到這裡,這時候剛好台大的夏鑄九老師經過,一聽到我提議台灣野百合,就說:「這個好!魯凱族認為這是勇敢純潔的象徵…」。其實當時學生的內規,是連老師都不能參與決策,不過夏老師這一小小的違規,牽動著投票一面倒。最後台大原提案數人不爽就撤離了,留下幾個私校的學生繼續討論,接下來怎麼辦?大家對於台灣野百合長什麼樣子一點概念也沒有,我雖然看過也怕畫不出來。情急之下我跑去跟這位和媒體熟稔的同學商量,看能不能調到一些野百合的照片,其中有一記者,他說很久很久以前有拍過,但要回辦公室找找看。現在回想起來,也不知他是誰?也不知被他的摩托車載去哪一個辦公大樓,總之在一個陰暗的辦公室中,他終於翻到幾張幻燈片,問我這是不是台灣野百合?我說:「就是這個沒錯,花瓣旁還有紅色的線條。」我們火速騎車衝回現場。回到會議中心,一位文化大學美術系的同學說:「又被推翻了!還是改回要做『鍾馗』,因為沒有人會做成立體造型的花,百合的莖太細了也可能立不起來!討論不出來怎麼做,他問我有沒有辦法製作或畫設計圖?我說:「我也沒辦法!我只會畫平面圖案,不會做立體雕塑!」但我還是把好不容易找到的幻燈片交給他。這時已接近天亮,因為衝鋒陷陣太急了,心臟開始絞痛,廣場醫療部也成立了,看了醫生,醫生說我連日疲憊心情緊張,要我放鬆一點,醫生開個鎮靜劑給我,他說睡一覺會好點。

1990年3月學運中開始的學生靜坐區。圖/鄧淑慧攝影提供
一覺醒來,沒想到又翻盤了!我看見有人從封鎖線外傳進布匹、鐵絲、木頭。我趕緊問文大的同學,不是說又要改做「鍾馗」了嗎?不知道是誰接手了製作台灣百合的精神意象,我只看見只要學生開出物資清單,外圍的民眾就一直傳送進來,分工速度效率之快,都不知誰是指揮者,誰是贊助者,只知道台灣民眾源源不絕地在支持場內自我封鎖的學生。睡袋、包子、便當、水應有盡有,還不時傳來加油聲,我們雖然看似被自囚在一條線的圈圈內,卻上演著一齣所謂的民主的大戲,在民主講堂的吆喝聲中,天黑時文化大學的同學又摸黑找我,他有點無賴地說:「你提議野百合,現在你要寫野百合的精神象徵!」。「什麼!為什麼是我要寫?」他說:「因為其他人也不知野百合有什麼精神象徵啊!你簡單寫寫,還會有人修改啦!」丟下紙筆就又消失在人群中,於是我就寫下——
台灣野百合
自主性—她是台灣特有種,象徵自由的精神。
草根性—從高山到海邊都有她的存在。
生命力強—在任何惡劣的環境中,她依然綻放。
春天開花—她在春天盛開,就在此刻。
純潔—純白的百合,一如學生為社會改革進步純潔的心思。
崇高—在原住民魯凱族中,她是尊榮的象徵。
(我寫了前面五條,印象中是夏老師加上第六條)
當天晚上「民主百合」做好了,推出廣場,感動眾人,自己也被眾人感動。全場熱血沸騰,那晚,那一朵百合雖然是不知名人士捐的白布、木條和鐵絲做的,但那意象,那個畫面永留在台灣人心中!從廣場撤離時,我有默默在百合花下許下心願!我有感覺,有人適合為這個社會改革、打頭陣,但我不適合。
今天推倒了一面牆,並不代表這個社會從此會變得美好,依然會有新的問題產生和存在。
一定要有人從文化的根基打起,
不管政權如何演替,不論政黨如何更新,
台灣人要有自我的文化意識,才能永續發展。
我在百合面前告訴自己,
我要做一個為台灣文化打地基的人。

製作台灣百合作為精神象徵,「民主百合」做好推出後感動所有人。圖/鄧淑慧攝影提供
回到學校的第一天,竟然看到東海校刊還有些黨報的社論寫著:這些學生受共產黨思想滲透,竟然引用毛語錄第幾章第幾頁,裡面有提到野百合做為精神象徵,居心叵測。我心裡想,你(編輯)才有看過毛語錄吧!我是只有看過蘭嶼的野百合,從來沒有看過毛語錄長什麼樣。為了平衡視聽,我寫了詳細的廣場日誌去投稿,結果被退件。後來這篇詳實紀錄的手稿也不知淪落何方了!
2021年12月30日,因為參觀翁金珠國策顧問所策劃的「民主台灣的街頭運動──彰化平原無名英雄展」無意中提到這段故事,國史館文獻館前館長劉峯松一再叮囑我要將這段經歷寫下來,他說還好3月學運不叫「鍾馗學運」,野百合能成為這個時代勇敢中求民主改革的精神象徵,令人感到欣慰。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