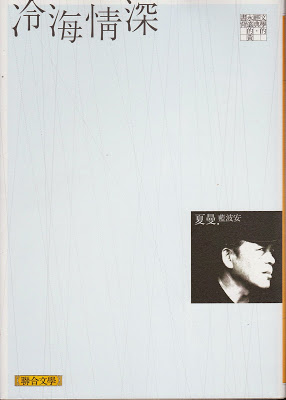《冷海情深》閱讀心得
一、
廢棄蚵架、保麗龍、垂釣客、淡灰色的天空。在我的記憶中,鹽水溪的出海口大多和它們脫不了干係,台江國家公園成立後,像是要在開發案將環境破壞殆盡以前爭睹這個島嶼尚且殘存的紅樹林生態最後一面,觀光船的行駛益發頻繁了,連我這個當地人都因為學校的戶外教學坐了幾遍。
觀光船是一連串經過設計的凝視,從四草出發,停靠探更寮,合力用吊罾拉起裡面通常空無一物的漁網,來體驗「漁民的生活」。接著,登上岸邊為了不打擾鳥類專門搭建的竹樓,從船家提供的望遠鏡裡觀看諸如白鷺鷥的「珍禽異獸」。整趟旅程的高潮在進入紅樹林瞬間開展,城市透過導遊的嘴巴在遊客面前展演,說著她尚未被現代性征服,還保有丁點自然的召喚。
唯有自己走上河面,才能察覺這樣的荒謬。有次西門國小舉辦了一梯泛舟活動,被朋友找去參加,兩人座的獨木舟在一段河道不得不停下來,長竹竿、保麗龍碎塊、酒瓶、浮腫的老鼠屍體、塑膠袋......眾多來自上游的廢棄物,儼然成了一個小型沙洲,以無庸置疑之姿聯手擋住我們的去路。幾年後讀了吳明益的《複眼人》才驚覺,原來那座從太平洋上巨大垃圾渦流中分裂而出、迎頭撞上台灣東海岸的「垃圾島」,其實早已悄悄的出現在我身邊。
二、
鄰居家的小孩提著一桶沙灘玩具站在門前,央求我帶他去附近玩。我伸出右手讓他牽著走,我原以為他要去的地方是西門國小,操場中央有個跳遠用的沙坑,但早就因為不知道什麼原因覆上草皮了。
「你想去那裡呢?」
「那邊有一個可以挖砂子的地方。」小孩手指校舍的方向。校門口的人行道正在施工,教室間的空地堆了些沙石,讓我想起小時候外公家旁邊的空地,這會是城市留給小孩最後的樂園嗎?
小孩用行動再次反駁了我自以為是的猜測,原來他的手其實指著更遠處的夕遊出張所,旁邊有個人工開闢的白沙灘公園,名字「鹽神」來自中間巨大的夙沙氏石雕,相傳為中國古代最早開始煮海為鹽的人,用以彰顯安平曾為重要的製鹽基地。這與地方脈絡斷裂的想像讓我有些困惑,上次在布袋洲南鹽場,他們供俸的可是土地公啊。
公園對假日想到海邊玩的家庭有著貼心的設計,沙灘、販賣部、洗腳池、沒有海浪,但為了保留海的意象,特別在旁規劃出一塊「嚴禁戲水」的水域,像是企圖假造出被馴服的孱弱大海,儘管在兩公里外,就是貨真價實的安平海岸線。
我不禁想起曾經聽過的一段話:「人類真是充滿妒恨的狹隘生物。由於人類只能在陸地上緩慢行走與生活,自古便羨慕天空與大海的生命,最後失去了生靈友伴的倫理,並透過囚禁他者來壯大自大的幻想。」於是乎因為這樣的妒恨,我們有了海生館,有備受喜愛的海豚秀,到最後,我們甚至驕傲到無以復加的圈養起一片海洋。
三、
長我廿來歲的表哥開我玩笑的說:「你在台灣接受漢人教育,漢人老師沒教你射魚的技巧與學問嗎?」
「當然沒有,漢人很怕海流,討厭海。」我笑著說。《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
有天到圖書館聽安平區前區長演講,概覽式的提過安平的一些老故事,他改談起港口打通後,正式轉為半個接近離島存在的漁光。和其他美麗的海灘並無二致,夏天的漁光總難避免傳出年輕人被海浪吞噬的噩耗,奇怪的是,幾乎都是台灣人。他玩笑似的提出解釋:「因為好兄弟是道教的,外國人信基督教,抓交替時不通。」
用宗教上的地緣關係來思考這個問題很有趣,不算太嚴謹,卻讓我想起某次的《海浪的記憶》讀書會。以夏曼•藍波安的書寫為基底,我們從語言的使用說起,從信仰的變遷、傳統文化在外來政權強勢影響下的崩解,聊到起自己與海洋的關係。朋友去澳洲東岸旅行過一段時間,同樣作為臨海的地方,那裡有著豐富的海上活動,以及相對台灣低得多的意外發生率,是什麼造成這樣的差異呢?「因為他們懂海。」
台灣呢?這是個被海洋環繞的島嶼(「靠海」這詞在消波塊面前顯得有些尷尬),理應有著豐富而成熟的海洋文化。至少很多人是這麼誇誇而談的,說台灣是個海洋國家。舊課綱裡,還曾經將海洋文化列為七個中文課本選文應該盡量顧及的「當代議題」之一,儘管出版社對海洋文學作家的想像似乎永遠只有夏曼•藍波安和廖鴻基。又或者,想像的貧乏,某種程度上也反映著海洋書寫的貧乏。
先後移往這個島嶼的住民,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彼岸的巨大板塊。陸地生活思維是太難變動的習性,即便《鹽田兒女》中那樣高度仰賴海洋的漁村,都得花費大把時間耕耘陸上的鹽田,更何況遠離海濱的農村。另一方面的原因,也源自於佔據六成以上面積的高山林地,在經濟生產中扮演了重要的地位。因此,年輕的移民,還沒來得及台灣島上發展出新生的海洋文化。我的意思是,如果「文化」這個詞彙,並非那麼中立的連為了啖食海鮮不惜破壞生態的病態熱愛都囊括進去,而是更一種更關乎永續的期待:體察海洋脈動的能力、憑依海洋的生活方式。
四、
父親很瞭解,他的孩子——達卡安資質並不差。凡是教他一件事,大抵都做得很好,令人滿意。想起達卡安的外祖父,在達卡安中年級以前,因疼愛而經常地帶他逃學,教她認識山裡的樹,海裡的魚,使得達卡安因而沒打好學校裡的基礎教育,落得每一學期都是班上倒數第一名。
「達卡安將來在競爭激烈的台灣社會裡,如何生存呢?」夏曼•達卡安每思及此,不由得鬱鬱寡歡了。《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
我想《冷海情深》整本書中最讓人難過的地方,大概莫過於兩種意念的強烈拉扯吧,一方面因為年輕一輩對傳統文化的疏離感到不安,見到熱愛海洋的孩子,卻又憂心他是否能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下過活。希望尋回文化根源的夏曼•藍波安,也因為來自家中關於生計的質疑掙扎不已。
台灣島上的我們,很幸運的不必面對同樣的衝突,但一如楊照在《複眼人》推薦序中所說:「依隨著山、海環境的毀滅,必然有連帶的,更複雜的毀滅,人與人感情狀態的毀滅。」環境不斷崩壞的現今,或許也是時候去思索,該用什麼樣的姿態來面對海洋。
從小被告知海邊很可怕,有很多暗流,盡量別靠近,因此對海感到陌生,甚至感到畏懼(而非敬畏),真正面對海洋的時候,就沒有人會懂得如何與海相處。只剩下課本上關於潮汐、海洋構造這些不經體驗,靠記誦或單向接受的「異化」知識。從教育做起的改變,會是相當重要的課題,畢竟都是有了瞭解以後,少了那些陌生與抽離,才會真正感到不忍,而有所珍惜的啊。
直到那一天,我們不再用大地囚禁海洋,用消波塊囚禁大地,終能擺脫為自己打造的牢籠,作為山與海的子民,獨立而自在地活著。
※文章轉載自【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閱讀台灣 探索自己」2015年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