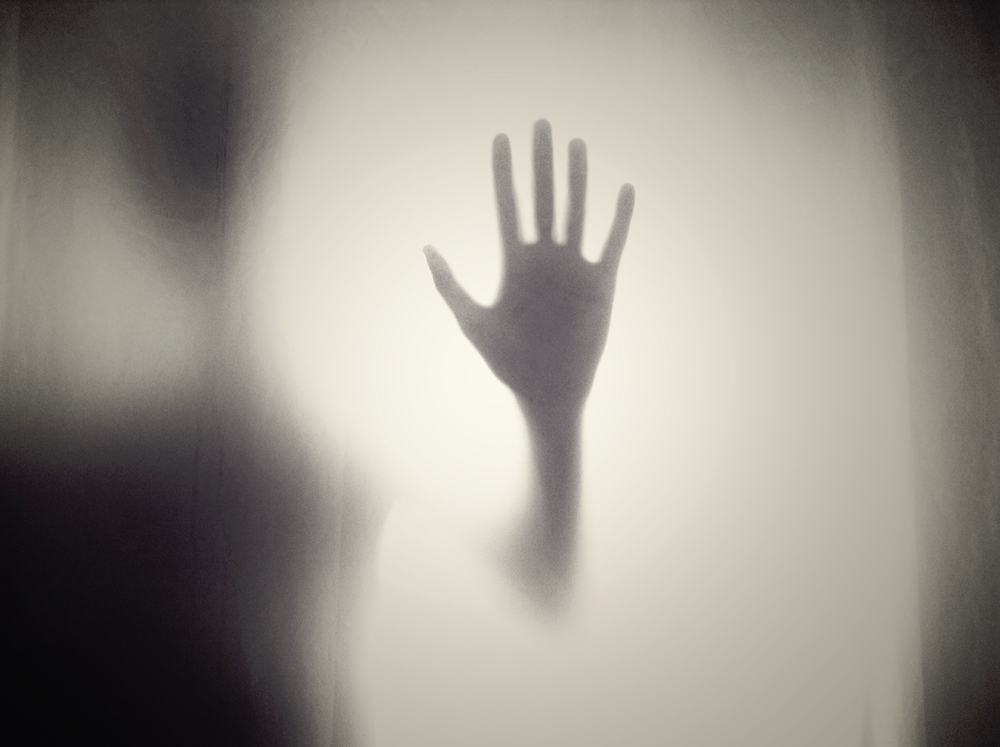一位天才女作家之死,引爆補教名師涉嫌性侵之疑雲,檢察機關雖已分案調查,但於事情發生已有相當時日,相關證據恐多滅失下,是否能有效進行訴追,實會有相當多的阻礙。而從此就顯示出,目前性侵案件於定罪上的困難。
依據刑法第221條第1項,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未有強暴、脅迫之手段,但卻藉由自己與被害人間的監督、扶助或照護關係,並因此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亦可處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於1999年後,刑法有關妨害性自主的犯罪,已由告訴乃論改成非告訴乃論,僅有在夫妻間犯強制性交罪仍屬告訴乃論,故告訴與否,原則上就不再是訴追要件,故檢察官不待告訴或告發,只要知有犯罪嫌疑,即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為主動偵查。
而於性侵害的案件裡,所能依賴的關鍵證據,當屬行為人於加害時,殘留於被害人身體的跡證,如血液、精液或其他可查驗DNA的身體組織。這些微物證據,因可能隨時消失,就得在第一時間採集,才足以讓鑑識人員獲得足夠的樣本為比對。而為了避免被害人因懼怕而不敢於出面控訴,於性侵害防治法第10、11條,更課予偵查機關及醫護人員,於採證與驗傷時,必須隨時注意對被害人的保護,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48條之1,被害人於偵查中受訊問時,亦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或社工人員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惟由於性侵害的被害人,或因創傷後徵候群,抑或是怕二次傷害,致造成報案與驗傷的遲疑或放棄,就可能因此喪失採證的最佳時機,亦使性侵害防治法與刑事訴訟法的保護規範,無用武之地。
也因此,於性侵害案件裡,被害人的陳述,就有很大的可能性,會成為定罪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證據。而為了防止被害人出庭所承受的壓力,依性侵害防治法第17條,就規定有被害人的身心創傷,若已達無法陳述的地步,法官即可以檢警的被害人筆錄為證,而成為傳聞證據排除的例外。只是此例外條款,不僅要件極為嚴格且為保障被告詰問權之故,適用機會不高,被害人仍以出庭作證為原則。
而雖然於被害人出庭之場合,性侵害防治法第16條,雖規定有適當隔離保護措施,以及不得詰問及提出被害人性經驗之證據,但被告方仍會在有意無意間,藉各種詢問機會,將案件導向是為利益、兩情相悅或者是愛慕的性交。則整個審判過程,就可能由對被告的定罪,轉向對被害人的道德指摘,若再加以物證缺乏,致須適用罪疑惟輕原則下,最終的判決結果,也有極大機率,是會以無罪為終,而與一般人的法感情相違背。
尤其此次引發討論的性侵事件,於被害人已死亡,所留下者,僅為以自我受害經驗所寫成的小說,到底有哪些是真實、哪些是虛擬,似也難於查證,恐連傳聞證據都構不上,欲定行為人之罪,實有極大的障礙,致僅能鼓勵其他受害者出面。只是於媒體已經大肆報導,且出面控訴者可能面臨緊接而來的輿論與司法機關調查下,就可能因此放棄告訴。也因此,如何有效降低刑事司法所帶給被害人的沈重壓力,肯定是當務之急。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法制上,進一步強化被害者的程序權保障,也是立法必須儘速檢討與修正的課題。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