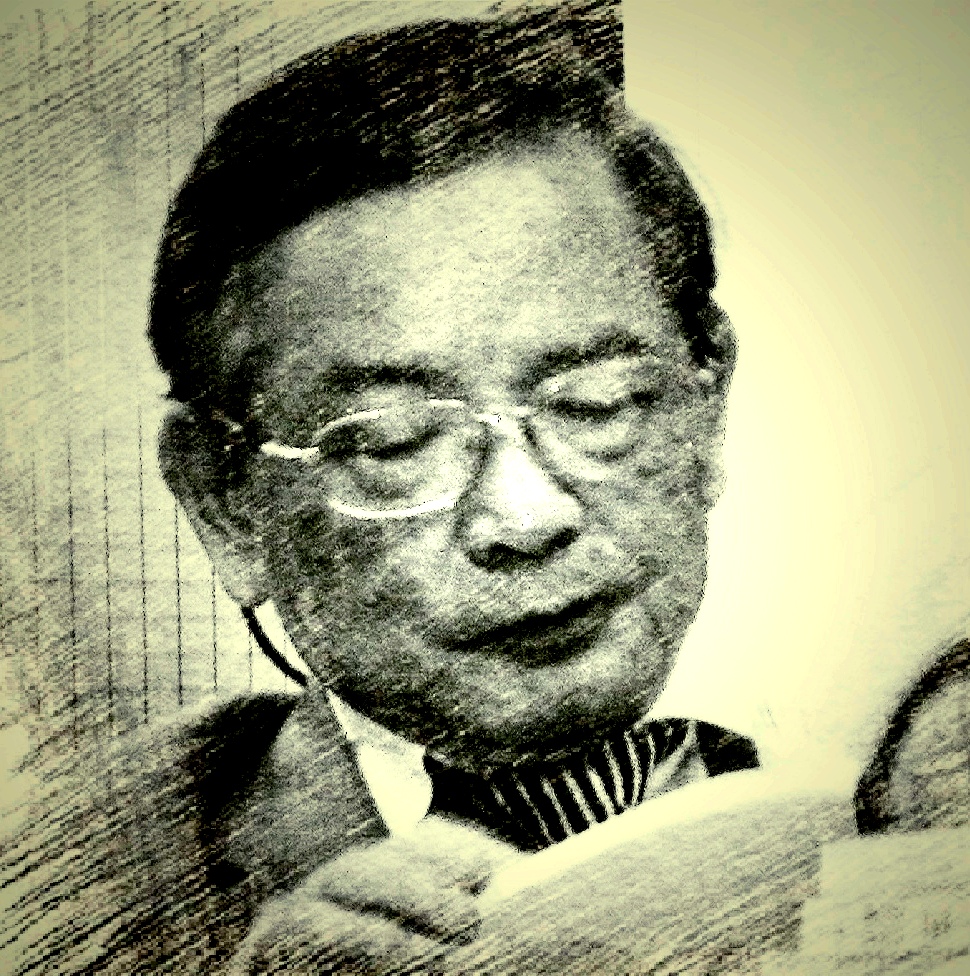愛默生與《美國文藝復興運動》
遠在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陸美國,在華盛頓帶領下,在1776年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獲得獨立,但是當時在文化上,美國人仍然是歐洲文化的殖民地,直到麻州的波士頓,出現了一位牧師出身、哈佛大學畢業的文化先知愛默生(1803—1882),在1837年,美國獨立之後61年,也就是他34歲那一年,他受《全美大學優等生協會哈佛分會》之邀,發表了一篇石破天驚的演講,題目是《美國學者》,在這篇演講中,他說:「我們美國人,做歐洲文化的殖民地太久了,我們必須從今天開始,創造我們美國人自己的文化和文學」,這篇轟動美國學術界的演講,日後被醫生作家《Oliver Wendell Holmes Sr.,1809—1894》譽為《美國文化的獨立宣言》,在美國文化界産生的影響力,不下於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在美國政治上的影響力。
愛默生是美國文化的傳教士,也是詩人兼哲學家,他精通希臘、羅馬文化,尤其受但丁的啓發最大;愛默生曽數度訪問英、法,與蘇格蘭的卡萊爾(1795—1881)和英國的田園詩人華滋華斯(1770—1850)成為知已之交,但是他仍然認為美國,必須以歐洲文化的精華的基礎上,創造美國自己獨特的文化與文學,果然在他的呼籲下,產生了《美國文藝復興時代》的來臨,獨立的美國文學有史以來第一次呈現多采多姿的繁榮景象,出現了梭羅、霍桑、麥爾維爾、惠特曼等文學巨匠,他們分別創作了:《華爾騰湖》、《紅字》、《白鯨記》、《草葉集》這樣一批代表獨立的美國文學的作品,它們不論在內容與形式上,都強烈地反映美國的民族特色與精神,影響所及,由於美國社會的多元化與包容力,到了廿世紀美國文學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奬的人數已經超過了英國。
葉慈與《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
愛爾蘭雖然是小國,但是因為有192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廿世紀大詩人葉慈(1865—1939)為靈魂人物,所推動的《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以1904年與友人一起創辦的Abbey Theater為中心,透過戲劇與詩歌的創作,努力打造愛爾蘭民族意識,把「愛爾蘭的寃錯化為甜美」,終於締造了光照寰宇的愛爾蘭文學,愛爾蘭的土地祗有台灣的90%,人口祗有台灣的四分之一,但從葉慈開始,他們的詩人和劇作家,總共有四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廿世紀最偉大的一部意識流小説《Ulysses》的作者,也是愛爾蘭作家《喬艾思,1882—1941)》,他雖然22歲時就流放法國巴黎,最後死在瑞士蘇黎世,但是他的小說題材都在寫愛爾蘭的人與事,這點有點像台灣作家郭松棻。
這場歷時五十年(1890—1939)的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又名塞爾特文藝復興《Celtic Renaissance》),這個運動致力於喚醒愛爾蘭意識,錘錬打造愛爾蘭本土的文化認同,與同時期政治方面的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有所交匯,又有所區隔;詩人葉慈甚至認為《愛爾蘭文化運動》取代了《愛爾蘭政治運動》,因為那時對《愛爾蘭自治方案》失望的年輕人,都紛紛投入《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中。葉慈剛開始寫詩時,以英國詩人史賓塞和雪萊為模仿對象的唯美派詩人,詩的背景不是飄渺的夢境,便是遙遠的國度,絲毫不見有愛爾蘭本土的色彩,直到20歲那一年(1885年),他邂逅了愛爾蘭民族文學之父歐李瑞(John O'Leary,1830—1907),葉慈才漸漸地把他的《文學之愛》和他對《民族國家的信仰》融匯貫通在一起,因為歐李瑞相信:「若要愛爾蘭獲得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獨立,愛爾蘭作家必須提供氣候,製造氛圍,創造一個明顯具有愛爾蘭特徵的民族想像。」於是他喊出一句廣為流傳的口號「沒有國家,就沒有偉大的文學;沒有文學,就沒有偉大的國家。」
因此他鼓勵愛爾蘭年輕人多讀世界經典以及愛爾蘭史地、詩歌和民俗故事。葉慈也是在歐李瑞的薰陶感染下,他開始正視愛爾蘭題材——愛爾蘭的古老神話和傳奇以及民間傳說和故事。果然在二年後,葉慈以古愛爾蘭的傳說做題材,創作長篇敍事詩《武信的流浪》(The Wanderings of Oisin),這部長詩為葉慈的一生文學事業,和整個《愛爾蘭文藝復興》奠定隠固的基石。而葉慈也深深感受到:「有獨立的愛爾蘭文學,才會有獨立的愛爾蘭」。
為了推動愛爾蘭文學,1891年葉慈在倫敦創立《愛爾蘭文學會》,1892年在都柏林成立《愛爾蘭民族文學會》,並開始出版《愛爾蘭叢書》,使民間大眾能夠加深認識本土傳統,1893年他出版《塞爾特微明》,吹起《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號角,1889年葉慈認識了,愛爾蘭女中豪傑兼革命志士茉德岡(Maud Gonne,1866—1953),受她的影響,詩人甚至在1896年加入革命組織《愛爾蘭共和兄弟會》,但是葉慈一生最大的貢獻,還是與葛列格里夫人、約翰.辛等人在1904年共同創立了《艾比劇場》(Abbey Theater),讓《愛爾蘭民族劇場》擁有一個正式的家,而《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規模與影響力逐漸擴大,尤其是葛列格里夫人,本來祗是文學愛好者,卻創作出愛爾蘭方言風味的英語,改寫民間故事,風迷一時,她説:「我寫作的目的,就是要幫助愛爾蘭增加尊嚴。」;葉慈也以古老的愛爾蘭抗英傳説,寫出短劇《胡拉洪之女凱思琳》(Cathleen ni Houlihan),塑造了一個雷霆萬鈞的民族運動神話,甚至不少年輕人受這齣劇的感召,而投入1916年的《復活節起義》。
總之,在《艾比劇場》30年的歷史中,不但啻造了愛爾蘭戲劇運動的黃金時代,也是愛爾蘭文藝復興的具體成果,結果使愛爾蘭人的民族意識日益高漲,最後終於在1922年,促成愛爾蘭政治上的獨立,脫離英國長達七百多年的統治;而在文學和文化方面,則締造了舉世矚目的《愛爾蘭文藝復興》,這個為時約半世紀之久的文學運動,以塞爾特(Celtic)傳統文化為基礎,致力於創造以愛爾蘭經驗為主的新文學,參加締造的著名作家包括:詩人葉慈、劇作家葛列格里夫人和約翰.辛以及辛.歐凱西、現代小說巨擘詹姆斯.喬哀思、小説家法蘭克.歐康納等人。而葉慈也在愛爾蘭成為獨立國家的第二年(192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奬的肯定,1931年他更獲頒牛津大學榮譽文學博士,1939年以74高齡去世時,英國詩人W.H.Auden在《悼念葉慈》一詩中惋歎:「瘋狂的愛爾蘭將你刺傷成詩。」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终於結束了,但是他所播下的文學種子仍然在開花結果,譽滿全球的愛爾蘭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89),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被譽為「葉慈之後最偉大的愛爾蘭詩人」奚尼(Seamus Heaney,1939—2013),也在1995年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
馬勒與維也納世紀末文化黃金時代
維也納之所以成為世界音樂之都,必須歸功於二位女皇后:瑪麗亞·特蕾莎(Maria Theresa,1717—1780)和伊莉莎白皇后(1837—1898)(被家人暱稱為茜茜公主),她們都是音樂愛好者,特蕾莎女王是哈布斯王朝,唯一的女性執政者,在她任內,國力頂盛,維也納的熊布朗宮和義大利斯卡拉歌劇院(1778)都是在她任內興建,她邀請六歲的莫札特到宮庭演出,留下一段佳話,由於她的熱愛音樂,使維也納到處都充滿了《音樂文藝復興》的氣氛,吸引了當時音樂大師海頓、莫札特、貝多芬齊集在維也納的現象,加上維也納土生土長的舒伯特和約翰·史特勞斯父子,終於在特蕾莎任內,產生了第一次音樂黃金時代,也讓維也納成為世界音樂之都。
伊莉莎白皇后,雖然沒有政治實權,但她是維也納藝文界的「文化偶像」,在她任內興建的維也納「皇家帝國宮廷歌劇院」(The Royal and Imperial Court Opera Theater),無形中成為維也納文化生活的重心所在,馬勒在擔任這個歌劇院音樂總監(1897—1907)十年期間,成為維也納文化界的龍頭老大,他在維也納的知名度僅次於皇帝,由於落伍的寡頭政治,使維也納政治上的進步停滯下來,大家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知識與藝術的追求上,一個為了文化的目的而存在的時代於焉形成,馬勒也就名正言順地成為藝術家的皇帝。
他帶領大家反抗頑固的保守派,成為年輕藝術家的明燈,一位當代的維也納權威人士說:「對我父母那一代人而言,馬勒時代是最幸福、最刺激和最偉大的經驗底時代。」,在社會上成為全能的文化人的馬勒,在文化掛師的奧國,地位之尊可想而知,當維也納《分離派》大師要替貝多芬做英雄雕像時,他心目中的模特兒便是馬勒,後來馬勒跟愛爾瑪結婚之後,才與《分離派》健將們密切交往,因為岳父摩爾便是《分離派》畫家之一,後來透過愛爾瑪的介紹,他與《分離派》負責歌劇舞台設計的健將Alfred Roller共創維也納歌劇院的黃金時代;《分離派》的兩位建築大師華格納(Otto Wagner)和魯斯(Adolf Loos)也是向馬勒的音樂看齊,把維也納古老的傳統裝飾拿掉,在他們新建築的外觀上鑲飾新的藝術作品。
當年維也納眾多名作家中,馬勒在他們心目中也是一位英雄人物,史尼茲勒、禇威格、霍夫曼斯塔爾等都是馬勒的祟拜者。在奧匈帝國,首都的精神生活也會影響到鄰近地區,因此馬勒透過維也納歌劇院散發出一種奮鬥和希望的氣氛,也影響到各行各業的藝術工作者,1907年12月9日,當馬勒結束維也納歌劇院音樂總監之職,前往就任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常任指揮時,他的三位親密子弟兵:荀貝格、魏本和貝爾格成立了《新維也納學派》,以新的面貌縰橫廿世紀樂壇,總之,世紀末的維也納,不管是音樂上的《新維也納樂派》,或是美術上的《分離派》,以及新建築、新文學的發展,都與馬勒息息相關,馬勒無形中成為世紀末維也納所有藝術家的精神領袖,可惜最後他還是被維也納的《反猶風潮》所擊敗。他走了之後,大家才開始懷念他所創造的《維也納文化的黃金時代》。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