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倒塌了30周年,不少人都在思考與詢問同一個問題:同樣發生在1989年,同樣發生在紅色共產黨政權下,為什麽東德的民主運動成功了?而中國的卻被鎮壓了?
世人常說: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說的是:國家興盛,是有根源的;國家滅亡,也是事出有因的。道理似乎簡單明了,成有成的根源,敗有敗的因由,但細究其根源與因由,就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得清,道得明的。按理說,柏林牆倒塌了30周年,這段歷史的枝節細末,被人筆錄了千萬遍,被人講述了千萬遍,一年又一年的故地重遊,一年又一年的故址瞻仰,我們居然還能「撿漏」,挖出了你我他不知曉的奇聞漏篇,且聽我們慢慢道來……
一雙特殊的採訪對象
11月10日晚上,我們原本約談了柏林著名的歷史學家瓦爾特•許斯(Walter Süß)博士。我們準時來到西柏林一幢老公寓的3樓,在門口笑臉相迎的卻是許斯夫人。步入充溢著濃濃書卷味的客廳,潔凈與寬敞,溫潤與靜謐,讓人感覺到陣陣的暖意與舒適。主客落座,寒暄一陣,便打開了話題,嗨……不聊不知道,一聊太湊巧了。
許斯博士是西德人,出生於1947年,曾攻讀政治學、社會學和東歐歷史,1979年獲得博士學位,曾任「西柏林日報」(Tageszeitung)記者,東歐研究所研究助理,從事蘇聯斯大林主義歷史研究項目,並曾在柏林自由大學中央社會科學研究所從事比較共產主義研究。自1992年後,許斯博士任聯邦史塔西(Staatssicherheit,簡稱Stasi)文件專員的科學助理,後升任該系系主任。他花了五年的時間,把史塔西的歷史和東德垮台之時,它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最後柏林牆坍塌的那幾天,為何這個讓人談虎色變的國安情報組織沒有「成功」地發揮作用「力挽狂瀾」,研究得極為細緻透徹,於2014年出版了那本《史塔西的終結(Staatssicherheit am Ende)》,引起社會的騷動和談論。今年他又出版了比較東德史塔西和蘇聯克格勃(KGB)的《史塔西和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對壘》這個大部頭的巨作。30年前,他在任西柏林日報的記者時,出席了1989年11月9日那場著名而戲劇性的新聞發布會,親歷了整個過程,事後還特意采訪了新聞發布會的主角、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SED)的中央委員、新聞秘書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確實是一位專家和重要的歷史見證人。我們能採訪他,內心極為激動。誰知他還介紹了他的夫人索尼婭,竟然也是當年直接參與「推牆」運動的健將之一。
許斯夫人索尼婭•許斯(Sonja Süß)是東德人,出生於1957年,醫學博士。當年參加了東德萊比錫的和平運動,是「民主崛起」(亦稱「民主破土」Demokratische Aufbruch )組織的領導成員之一,後擔任萊比錫民主運動發言人。許斯夫人當時撰寫博士論文已畢,並在精神病學研究機構中工作。自1997年以來,她在柏林擔任精神病醫生和心理治療師。許斯夫人的專業著作是個非常敏感的話題:《被政治濫用了嗎(Politisch mißbraucht?)》,研究東德政府是否曾以精神病學為手段,來脅迫恐嚇異議人士。1989年東德的民主運動浪潮掀起時,她一直在組織舉行示威抗議活動,特別是那場10月9日的萊比錫示威抗議,為一個月後推倒柏林牆拉開了序幕,她同樣是一位在場的重要歷史見證人。

上世紀九十年代許斯夫婦。圖/作者提供
了解到這些詳細情況後,我們十分激動,他倆都是當年柏林牆倒塌時的親自臨場的證人,而一個是西德人,一個是東德人,一個是當年歷史性的新聞發布會的在場記者,一個是當年東德萊比錫示威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真所謂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們即刻修正了采訪方案,同時采訪許斯夫婦兩人。
一支煙摧毀了柏林牆的封鎖
估計「一支煙摧毀了柏林牆封鎖」的說法,應該鮮為人知,許斯博士講述了這故事背後的前因後果。
許斯博士回憶了1989年11月9日那個晚上,在東柏林的默恩大街(Mohrenstraße)36-37號樓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所發生的一切。
新聞發布會原本完全有另外一個主題,當時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SED)正面臨危急存亡之秋,面對大批逃亡潮所形成的人心散瘓,百廢待興的局面,緊急召開了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討論應急對策,提出改革方案。主持記者會的人是中央委員兼新聞秘書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記者會主要是報告改革政策的內容,差不多有150記者在場,記者許斯來遲了,坐在最後一排。

1989年11月9日晚上,在東柏林的默恩大街36-37號樓舉行的新聞發布會,許斯博士坐在會場最後一排。圖/作者提供
沙博夫斯基出生於1929年。1978年至1985年擔任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黨報《 新德意志報》(Neues Deutschland)的主編,也曾擔任東柏林地區管理局的第一書記。從1981年到1989年,沙博夫斯基一直是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中央委員會成員,198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在1989年危急當兒,他臨危受命,於11月6日起擔任新聞秘書,作為政治局的發言人。沒想到上任三天,就把一個國家毀了。
新聞發佈會接近尾聲時,沙博夫斯基看了一下表,他還想講一點剛剛發布的新旅行法規定,三天前11月6日他作為新上任的新聞官,在《新德意志報》上發布了有關新旅行法的修正草案,按照新規定,每一個東德公民若在西邊有親屬,允許每年赴西德逗留幾天,或者幾周,這是計劃中的修正案,但尚須最後經政治局通過。這裏必須提一下當時的背景,在中央會議上,於10月17日才接下昂納克(Erich Honecker)的總書記位置,並當上東德國家元首的埃貢·克倫茨(Egon Krenz),對修正案提出幾了點意見。而記者會當天上午即11月9日,內政部的人民警察的高級官員Gerhard Lauter,認為要救「沈船」,必須開放邊境,於是自作主張,又擬定了一個附加的新規定,並呈交上報,裡面有好些條文,其中強調每一名東德人,不論有沒有親屬在西德,都可以離境到西德和西柏林去。這個新規定,由於局勢混亂緊迫,草草地就被中央委員會通過了。到了下午克倫茲把通過的文件塞到沙博夫斯基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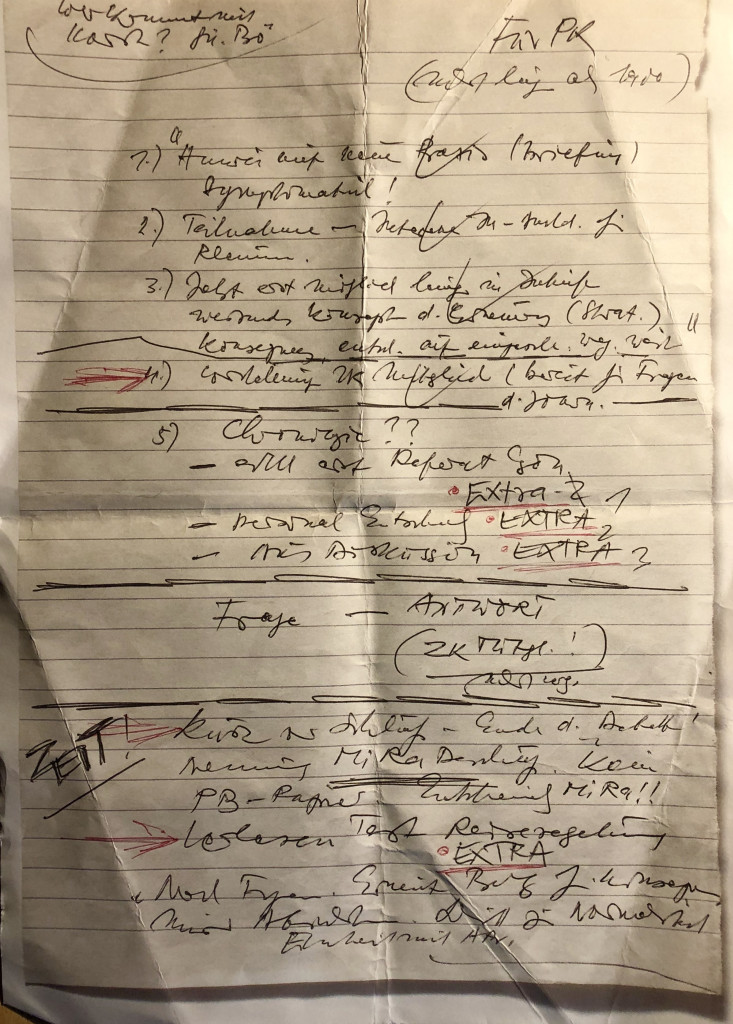
新聞發布會上沙博夫斯基手持的那張紀錄紙的複印件。圖/作者提供
許斯博士說,沙博夫斯基在記者會上雜亂地翻閱手中好些文件,大約在諸多議題中,匆忙地沒有細讀旅行法的這一條,他順口說,太長了,我就不一一宣讀了,政治局通過的這個規定,允許東德公民出境到西德和西柏林去。其實在中央會議上,埃貢·克倫茨在會上就新旅行法發言時,沙博夫斯基恰好跑出門外抽煙去了,漏聽了部分重要內容。起草者的原文上寫的是,該規定將從次日生效。
而沙博夫斯基根本不知情,卻作了如上公布,這時有一個意大利記者提問:何時生效?沙博夫斯基翻了一陣眼前的文件,結結巴巴地說:「據我所知……立即,立即生效」。又有提問說:是否也適用於西柏林?他答道:「是的,是的,當然。」這下惹惱了蘇聯人,東德政府只可以決定東西德的邊境,但是東西柏林邊境是由蘇聯人與盟國管理的,這是個嚴重錯誤。
這裏的問題是:1、東德政府確實有取消限制的計劃,由於當時有大批東德人經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逃往西德,迫使東德政府不得不取消外遊限制,但並非即時生效,原定具體規定將在翌日通知所有單位。2、還需要在警察局辦理申請手續,簽證等。
當晚的新聞於臨近深夜時,沙博夫斯基那句話:東德人可以去西德和西柏林,並且「立即生效」一經播出,就如炸彈一般炸開了圍牆和鐵幕,東德民眾穿著睡衣拖鞋就奔向圍牆,戒備森嚴的東德邊防軍一時目瞪口呆,面對潮水一般歡呼狂叫的人流,措手不及,只能雙手放在背後,尷尬地木然站著,保持沈默。這時西柏林的市民也蜂擁到圍牆邊,兩邊人民爬上牆,互相擁抱雀躍,有些東德人把家裡的「國產車塔比」(Trabi)開出來,徑直穿過邊界,到達西邊,西柏林的人夾道歡迎,給他們遞上啤酒和鮮花,甚至西德馬克。黑夜過去,天亮之際,世界看到一段動人的歷史終結場景,柏林牆歷被東德的人流沖垮了,意外地開啟了兩德統一的序幕,接連著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個倒也倒也,連蘇聯帝國也分崩離析了。

主持記者會的東德中央委員兼新聞秘書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圖/田牧
沙博夫斯基的一支煙惹出了禍端,只聽過酒後誤事,不想煙後也有誤事的,豈不是一支煙摧毀了柏林牆封鎖,導致柏林牆突發垮塌,也為此,不久前才獲得馬克思勳章的沙博夫斯基,隨即被逐出德國統一社會黨。仔細想想也不覺得驚訝,歷史上的這類事件還真不少,中國人自譽的「萬裏長城」,還不是數度被攻破。法國固若金湯的馬其頓防線,用了50億法郎與10年建造,照樣被德軍不攻自破。
萊比錫的89民運高峰
東德民主運動的掀起,與北京的八九民運緊密相連。
從官方來說,東德議會明確表示支持中國政府的立場,他們的公開聲明中將中國軍隊屠殺大學生的事件稱為:「鎮壓反革命的行動」。「六四」事件過去一個月,沙博夫斯基代表東德政府訪問了北京,他肩負著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昂納克的兩項使命:一是向中國政府轉達昂納克對「成功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祝賀」;二是要弄清楚「天安門廣場上到底發生了什麽?」不是說東德不相信北京采取了強硬手段,而是希望「取經」,采集與尋找第一手資料,以便參考。
從民間來說,北京的「六四」事件發生後,東德老百姓對天安門的血腥鎮壓,做出了同政府完全不同的反應,在中國駐東柏林大使館門前,有20多名試圖向大使館遞交抗議信的人被逮捕,兩周後再次有中國使館前示威者被捕。
許斯夫人詳細介紹了1989年的萊比錫民主運動情況。她介紹道:她參加了民主崛起組織,他們組織的目標並不是推翻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的領導,他們需要社會改良與改革,這種民間的聲音越來越強烈。她說:剛開始我們的活動,是在教堂舉行,有時也會在某人的家裏舉行。而10月9日那一天,這是個難忘的日子,這天活動安排在火車站前的廣場上,我們自己事先估計可能會有幾百人參與活動,出人預料的是,工人、學生、知識分子、普通市民等越聚越多,最後達到七萬多人的和平示威,占領了萊比錫市中心。
作為組織者,我們特別擔心出事,北京「六四血案」就是教訓,我們宣布嚴格的紀律,必須堅持和平理性的示威抗議,絕不允許動武。我們這些組織者,不僅需要看顧整個示威群體,不能在隊伍中出現棍棒鐵具等,同時還得十分警覺,全神註視警察的一舉一動,看他們是不是會動手拿槍。許斯夫人是醫生,她已獲悉,他們的醫院裏準備了大量血漿,因為有跡象表明政府可能會鎮壓。就在一週多前,中國國慶日時,東德派出了昂納克的接班人克倫茲到北京去祝賀,讚揚「中國式解決模式」(chinesische Lösung)處理危機,出動軍隊「維持秩序」,因此東德的反對派人士有理由相信,萬一對峙局勢緊張,東德政府會採用「中國式解決模式」,進行血腥鎮壓。
後來我們知道,其實政府與警察也十分緊張,怎麽突然出現了這麽大規模的、遠超出他們預料和估計規模的示威抗議活動,但是政府還是不準備采用「中國解決模式」。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萊比錫交響樂團的指揮家Kurt Masur打電話給克倫茲,警告他,不能流血,不能殺戮,還有一些著名的演藝人士也都站在前沿陣地,堅決抵制暴力鎮壓。萊比錫福音教尼古拉教堂(Nikolaikirche)的著名牧師Christian F. E. Führer,一向主持示威活動,並極力保護群眾安全,他說,我們的祈禱上達「天聽」,這上帝對東德地區和平示威是極力佑護的。他還說:1989年的10月9日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10月9日那一天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後來在西德電視台也有報道,這樣的宣傳很快在整個東德的土地上,如火如荼地傳播開來。
多年後,沙博夫斯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證實,1989年10月,當越來越多的人走上街頭時,政治局中的確有一些人表示,必須將這場抗議行動宣布為「反革命暴亂」,並採取行動。然而當時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地位已經搖搖欲墜了。
柏林牆垮塌的社會原因
愛因斯坦不相信偶然一說,他說道:沒有僥倖這回事,最偶然的意外,似乎也都是有其必然性。錢鐘書也有略似的說法:天下就沒有偶然,那不過是化了妝的、戴了面具的必然。

許斯博士手持他的兩本歷史書籍。圖/作者提供
那麽柏林牆垮塌背後的必然性是什麽?
許斯博士說了四個原因:
一是改革開放政策。那時蘇聯戈爾巴喬夫提出「新思維」的改革開放政策,給了東歐社會主義陣營政權很大的觸動,並產生了憂慮與警覺。因為原先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背後有蘇聯支撐。比如:1953年東德發生了「六一七事件」,從東柏林300余名建築工人經濟罷工開始,不幾日示威抗議遍及東德各大城鎮,最後蘇聯駐軍出動坦克上街,驅散示威群眾,釀成55人死亡的流血慘案,至今在柏林還有一條通往布蘭登堡城門的街定名為「六月十七日街」,就是為紀念這個歷史事件。還比如匈牙利十月事件,發生於1956年10月23日-11月4日,匈牙利民眾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政府表達不滿,導致蘇聯出兵鎮壓,當時逃離國境的匈牙利菁英,至今還散佈在歐洲各地,不過1989-90年革命成功後,許多已經老邁的當年流亡人士已經返回自由的家園。再比如捷克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1月5日,從捷克斯洛伐克國內的一場政治民主化運動開始,直到當年8月20日,以蘇聯武裝鎮壓告終。東德政府非常清楚,這些國家發生反政府事件,都是蘇聯出面鎮壓下去的。但是眼下蘇聯自己卻實行改革開放,這讓東德政府非常矛盾,一方面東德政府需要蘇聯的靠山,另一方面又擔心蘇聯的改革政策動搖社會主義傳統的統治模式。而對民主派、或者說反對派人士來說,他們歡迎戈爾巴喬夫「新思維」,認為他是好樣的。
二是經濟因素。東西德緊鄰,但經濟狀況迥異,西德經濟遠遠超過東德,東德的國有經濟一塌糊塗,已經窮途末路。有資料顯示,從70年代直到80年代末期,東德經濟發展速度開始變慢,1989年時,東德人的實際收入只有西德人的不到三分之一。東德政府每年向西德政府大量貸款,東德需要依靠西德政府年年的輸血,才能茍活生存,所以東德政府也不可以太過分地實施收緊政策,過猶不及,可能導致西德政府停止對東德的經濟輸血。
三是媒體影響。雖然當時沒有網絡,但是電視、電台節目還是很有作用的,雖然也有蘇聯節目,但畢竟存在語言問題,東德民眾喜歡觀看西柏林的電視節目,收聽西柏林的電台節目。這是東德政府無法控制的。許斯博士後來采訪沙博夫斯基,後者坦言道: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時,差不多每個成員都在看西德的新聞廣播與文藝節目,無形之中,他們無法將自己僵化的意識形態強加於老百姓,東德的官員都受西德的影響。這是重要的原因。

索尼婭•許斯博士手持她的一本心理學書籍。圖/田牧
許斯夫人提到的10月9日萊比錫抗議活動,西德電視都播出來了,這又反過來帶動了東德其他城市的民主運動。當然這些攝像不是西方媒體拍攝的,他們是嚴禁到這種現場出現的。當天有兩個柏林年輕人背著攝影設備,冒險爬上高樓屋頂,自上而下進行全錄,然後帶到西柏林播放。著名詩人比爾曼在自傳《唱垮柏林牆的傳奇詩人》一書中,也描述了這個場景。
四是宗教因素。西方的宗教,曾經是政教合一,後來政教分離,政權是不能管理與統治教會的,相反地,宗教一方面擁有監督政權的權利和責任,另一方面教會能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比較自由的空間與場所,還能起到安全保護作用。東德的解體教會就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像天主教國家波蘭,在推翻共產專制體制上,教會發揮了極大的作用,這是有目共睹的。
五是官員內部的變化。1988年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開放政策,對東德造成非常大的沖擊,它在經濟上相當依靠西德,政治上發生了動搖,社會主義慢慢變色,已無法繼續維持原來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而且政府部門的官員,或者警察也有憂慮,這樣壓制民眾,屆時世道變了,我們怎麽辦?也就是說政府內部也已經發生了蛻變。
許斯夫人補充道:那一階段,國家幹部、政治家內心也處於左右徘徊,也不知道走什麽路?這個層面的人也已開始動搖,忐忑不安,有些比較開明的政府官員,以私人名義也會去教堂參加和平祈禱會,他們希望從那裏得到啟發,吸取養料,他們心裏思考的,不是推翻這個政權,而是改變改良這個政權,讓這個「走上歧路」的政權變得更好。
我們的思考
中國的八九民運為什麽會失敗?
一是人的因素。無論是東德,還是前蘇聯等,民主運動的主體成員,除了大批的知識精英積極參與以外,還有一大批政權體制內的官員參與,形成了能主導與掌控整個運動方向與態勢。而中國雖然有,但是嚴重缺失,相反也說明了中國統治者的頑固性與反動性,危急時刻,中共執政者絕不手軟,必然下令武裝鎮壓,來個玉石俱焚。而東德的、前蘇聯的執政者和東歐各個共產國家都最終沒有下這樣殘酷的鎮壓命令。
二是宗教因素。西方的宗教,政權是不能管理與統治宗教,教會為社會運動提供場所,並起到安全保護作用。而在中國,自古皇權就淩駕於宗教之上,毛澤東就說過「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唯物論的共產主義者是對天地萬物都無所敬畏的,他們只要抓住手中的權。就眼下的中國來說,政府還搞出了「愛國宗教」,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是他們的信條。因此一些信徒與神職人員時常被政府抓捕與判刑,這在中國是家常便飯,見怪不怪。
三是時機問題。如果中國的八九民運推遲一年或者兩年的到來,有了東德、東歐、前蘇聯的榜樣,中國的民主運動就有了參照目標與榜樣,成功的概率會大大增強與增大。所謂的韜晦待時,或者說待時而動,這就是個機遇問題。不過中國的八九民運,還是為東德、東歐、前蘇聯提供了榜樣與經驗,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輝煌一頁。
影音連結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