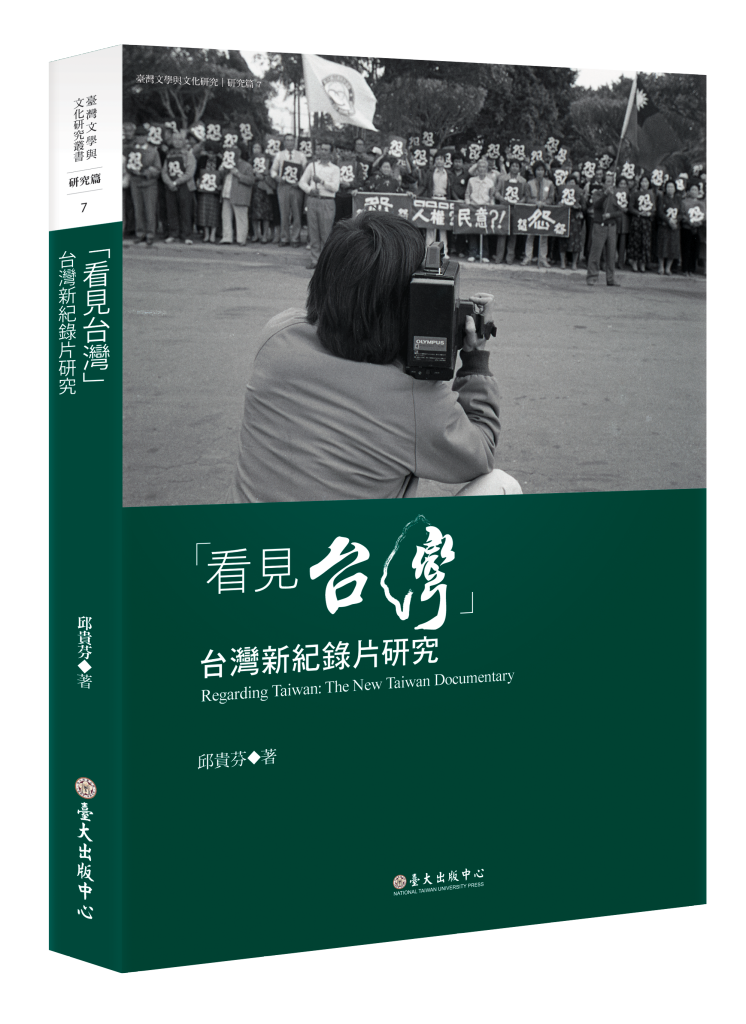如何看見,我們原本看不見、未能看見或視而不見的台灣?
紀錄片提供了看見台灣的新的角度與方式,
然而我們又如何「看見」紀錄片中的洞見與不見?
在1980年代中葉與台灣新電影幾乎同時出現的台灣新紀錄片到底有何可觀之處?與台灣新電影的觀賞或解讀方式有何不同?這些「新」紀錄片之「新」,如何界定?歷經三十年的發展,是否形成特有的傳統?經歷了哪些階段的發展?開發了哪些台灣紀錄片獨特的研究議題?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和值得探討的問題?與其他東亞的紀錄片相較,台灣新紀錄片展現了哪些特色和侷限之處?「國際發聲」的可能與挑戰為何?本書除了探討這些問題,也澄清「紀錄片」的定義和研究方法,引導讀者進入台灣紀錄片的場域。
全書分五大章節:導論、歷史紀錄片、環境紀錄片、記錄倫理、以及台灣紀錄片的國際發聲。書中討論的數十部作品涵蓋各類型紀錄片,導演跨越不同世代、族群與性別,包括柯金源、馬躍‧比吼、比令‧亞布、蕭美玲、賀照緹、李香秀、簡偉斯、沈可尚、簡毓群、齊柏林、楊力州等。
第一章:導論(摘錄)
紀錄片的定義與特質
紀錄片的研究方法和劇情片的研究有所不同。進入影片細節討論之前,有必要在此釐清一些定義和基本概念。
與劇情片不同的是,紀錄片研究遭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永遠是:「紀錄片是什麼?」紀錄片的定義之所以成為問題,主要因為紀錄片一般被視為「現實的忠實記錄」,紀錄片和「現實」的關係衍生了一些理解紀錄片的問題。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卻需要一層層來剖析、回應,從中釐清對於紀錄片的一些基本知識。
一、紀錄片呈現的不是虛構的世界和人物,紀錄片與真實世界有一定的連結。透過紀錄片與劇情片的比較來理解紀錄片的範疇,不失為一個有效的方法。如同Bill Nichols所言:「紀錄片的定義總是透過『相對的』、『比較』而得來。」(2001: 20)最簡單地說,劇情片是純然虛構的,觀眾不會把劇情片裡所搬演的人、事、物當真,但是,當觀眾看紀錄片時,期待紀錄片所呈現的不是虛構的人物和事件,而是現實世界所發生(過)的事,曾經存在過的人、事、物。這個與現實世界的連結,是紀錄片最大的魅力所在(B. Nichols 2001: 27)。John Corner也提到,鮮少有紀錄片導演願意放棄「紀錄片指涉現實世界」這個紀錄片之所以為紀錄片的基本(1996: 22)。可想而知,如果《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不是劇情片而是紀錄片的話,觀眾觀看時的解析方式和回應會有多大的不同。反過來,如果電視所呈現的911恐怖攻擊或是日本福島海嘯及之後的核能災難是劇情片,我們的解讀也將有所改變。
二、紀錄片與現實世界有所連結,這並不意味紀錄片必然以「呈現現實世界」為目標。創作型的紀錄片往往以現實世界的人、事、物為基本素材,卻以特殊的美學形式,強調紀錄片作為一種具有強烈個人風格的「作品」,這也無可厚非。張照堂1970年代的《王船祭典》是很好的例子,孫松榮視之為台灣此類紀錄片的「先驅」,也曾撰文進行精闢的分析(2014:95-7)。而周美玲策劃的《流離島影》系列是台灣新紀錄片歷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不過,李道明的一段話提醒影像工作者,不可因耽溺於形式美學的追求而忽略了這個重要的紀錄倫理問題:
「不誠實」其實正是對一部紀錄片的作者所能提出的最嚴厲的指控。我的基本觀點是,紀錄片作者與觀者之間應該存有一種默契(tacit understanding),即紀錄片所再現的影像是來自攝影機對真實世界的捕捉。任何對真實世界的偽造、扭曲、干預或甚至重新創造,都被認為是不適當的,會引起觀者的強烈抗議,除非紀錄片工作者對他/她的作為善盡告知觀者的義務……在追求紀錄片新形式的過程中,……如何不會對真實世界進行偽造、扭曲、干預或甚至重新創造,……是台灣所有紀錄片作者應該自我期許的目標。(李道明2006c:76)
三、紀錄片有所謂「紀錄倫理」的考量。紀錄片當然也可能採用劇情片的許多手法,包括說故事、劇情鋪陳、影像與聲音的美學安排等等,但是,如果紀錄片呈現的是一個虛構的人物或事件,但觀眾卻被矇在鼓裡,這就涉及紀錄片製作的倫理問題。這也是為何當觀眾發現吳乙峰的紀錄片《生命》裡,導演吳乙峰的化身敘述者「我」一直對話的「朋友」,其實只是個虛構的人物時,引起不少爭論的原因。如同Patricia Aufderheide所言:「真實和可信度是紀錄片的特質,而紀錄片之所以受到重視,也因為這個影片類別具有這些特質。紀錄片之所以不能欺騙觀眾,是因為觀眾可能會根據紀錄片所提供的訊息而在現實社會裡採取行動,產生現實世界裡的效應。紀錄片不僅幫助我們理解我們身處的世界,也形塑我們的公共參與角色」(2007: 4-5)。
四、雖然紀錄片在手法上無論再如何「創意」和「實驗性」,都不可刻意「以假亂真」,而必須與現實世界有某種連結,否則影片作為「紀錄片」的歸類便會產生問題。但是這並不表示說,紀錄片就等同於真實世界。我們需釐清「影像紀錄」和「紀錄片」的差別。紀錄片基本上是音像作為媒介的再現模式,但經常被視為一種「紀錄」(record)或文件(document)。紀錄片(documentary)並不等同於文件。後者指涉現實世界裡的某種證據,而前者強調的是把證據「編碼」的過程,透過脈絡化的論述,把這些證據加以組織成某種具有結構的影像論述(P. Rosen 1993: 72-5)。Stella Bruzzi 在New Documenta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裡對此問題有詳細的討論。影像紀錄雖然忠實攝錄了真實世界曾經發生過的人、事、物,但是,這些影像其實並無穩定、不辯自明的意義。影像意義的產生,來自於影像被置放在特定的脈絡。同樣的影像紀錄放在不同的脈絡,經常產生不同的意義(S. Bruzzi 2000: 13-21)。紀錄片組織影像和其他史料,產生某種具有結構的再現,也因此賦予這些影像意義(S. Bruzzi 2000: 22)。
台灣導演賀照緹這樣說明她對於「紀錄片」的認知:「我認為紀錄片是一個有觀點的文本,是帶著紀錄片導演的觀點所製作出來的影片,不是一個客觀的影片,而且紀錄片的製作團隊不會迴避自己的觀點。」而她也針對「紀錄片」和「新聞報導」的關係提出她的看法:「很多人會問,紀錄片和新聞報導有什麼不同?一般來說,比較大的不同在於紀錄片花比較長的時間去做田調,整個研究的過程較長、挖的深度也比較深。但我不覺得公民記者和紀錄片的差異性一定是這麼大,公民記者也可能拍一部紀錄片,有可能超越個人化的紀錄分享,也有可能深度深、具有很好的切片角度。我認為,公民媒體也會是紀錄片的一部分,兩者不是截然劃分的兩種類型。」(王思涵、王昀燕、禹鐘月 2014)
五、所以,總括來說,「紀錄片有關真實世界,而不是真實世界」(documentaries are about life; they are not real life)(P. Aufderheide 2007: 2)。目前紀錄片研究者的共識是:紀錄片是導演以現實世界作為材料,把素材加以篩選組織,表達某種觀點的現實世界的再現。換言之,紀錄片不是客觀的事實,而是具有觀點的現實再現(represen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world)。沒有絕對客觀、不具觀點的紀錄片。如同Erik Barnouw 所言:「紀錄片製作涉及無數的選擇,選擇哪些影像、用什麼樣的角度錄製這些影像、影像如何剪輯、聲音如何安排、訪談如何進行和篩選……等等。每一個選擇都已經隱含某個企圖和動機,暗示了導演的某種觀點」(E. Barnouw 1993: 344)。總而言之,紀錄片不僅是影像紀錄,紀錄片是具有結構和觀點的現實世界的呈現。即使是觀察式的紀錄片,也不是「客觀」的現實複製。觀察(observation)與客觀(objectivity)不可混為一談(S. Bruzzi 2000: 69-70)。而紀錄片如何再現現實世界的人、事、物?表達了什麼樣的觀點?希望達到什麼目的?這些問題便成為紀錄片研究的重要課題。實驗型的紀錄片,往往更強調「真實與虛構」界線並不穩定,凸顯形式,但也不免涉及這些紀錄片研究的基本課題。
六、由於紀錄片與現實世界的連結,紀錄片的攝製因而涉及種種「倫理」問題。「倫理」課題是紀錄片拍攝與討論的重點,也是紀錄片的特質。紀錄片的倫理課題,不僅涉及如何取得現實世界的影像,求知的權利和保有隱私的權利可能的衝突,更有導演對於被拍攝者、觀眾的責任,以及其他種種拍攝行為的倫理(B. Nichols 1991: 77)。紀錄片的觀看永遠涉及觀看政治和倫理(politics and ethics of the gaze)(B. Nichols 1991: 77)。許多紀錄片的拍攝動機來自於「為弱勢發聲」,這基本上是一種倫理行動,不再只執著於主體的存有(being),而採取行動來回應他者的需求,視此回應(response-ability)為責任(responsibility)(D. Perpich 2008: 87), 這是法國哲學家Emmanuel Levinas所說的倫理:主體最重要的結構不在於「我」,而在於對於「他者」的責任(E. Levinas 1998a: 9-11)。根據Levinas 的倫理學,主體超脫對於主體「存有」(being)或「存在本質」(beingness)的關懷,而把生命的重點移到「我和他者的關係」,人生最重要的課題,不必然是「自我追尋」,而是「如何回應(弱勢)他者的需求?」「如何把他者當作我的責任?」(E. Levinas 1998a: 8-9, 1998b: 29; A. Peperzak 1993: 131; C. Davis 1996: 78)。許多紀錄片拍攝的動力往往基於「為弱勢發聲」這樣的倫理動力。而由於「他者」是紀錄片的關懷,如何避免影像編碼的暴力,如何避免把「他者」收編到自己的知識和論述裡,如何讓「他者」現身,如何回應「他者」的需求?這些是Levinas探討「倫理」時所提出的重要課題,也常常是紀錄片念茲在茲的問題。
正因為倫理課題對於紀錄片構成的重要性,因此,紀錄倫理是紀錄片研究的重要議題。如果吳乙峰的《生命》引發的爭議來自於紀錄片導演對於觀眾的承諾和責任,楊力州《水蜜桃阿嬤》(2007)涉及的倫理問題或是蕭美玲的《雲的那端》、胡台麗的《蘭嶼觀點》(1993)的反思,則環繞著紀錄片導演對於被拍攝者的責任。被拍攝者的權利是否有妥善的維護,或是受到鏡頭的暴力與剝削?這是紀錄片工作者不可迴避的問題。王智章指出,1980 年代「綠色小組」錄製影像時,刻意「在520的錄影帶中,就將民眾拆、打立法院招牌的畫面剪去不播」,以避免影片淪為警方蒐證的工具,「保護反對運動者免受司法的迫害」(張碧華 2000:322)。倫理的課題被視為比「客觀紀實」或是「平衡報導」更為重要。紀錄片導演對於這些倫理課題的敏感度、處理態度和反思行為,是紀錄片研究關切的議題。
即使紀錄片不必然都背負了沉重的社會使命,以紀錄片作為一種個人創作和藝術的表現模式,也是紀錄片的重要類型。但是,紀錄片作為一種藝術或創作,無論再如何創新和實驗,都不可忽略「紀錄倫理」。這提醒我們紀錄片與真實世界無法切斷的連結,紀錄片與虛構的劇情片的界線,雖然可能模糊,卻無法完全泯滅。我想不厭其煩地再次引用李道明的洞見和提醒:「實驗本身未必就足以證實自己的正確或更具開創性。……我認為必須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把實驗影像、動畫插入紀錄片的結構中,這樣做是否更能達成『紀錄片』本身上的意義或目的?」研究中國電影的史丹福大學教授王斑也提醒我們,視紀錄片為虛構,輕易取消紀錄片與劇情片的界線,並無助於我們探討紀錄片這種特殊電影形式所帶來的深刻課題。他提出這樣的一個紀錄片的定義和特色:「紀錄片與文化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所主張的『所有的東西都是一種風格或虛構』這樣的理念背道而馳。」(Documentary runs counter to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nihilism inherent in the view that“anything is a style or fabrication".),他認為紀錄片和真實世界有不可切割的關係,因為紀錄片是「一個具有風險的實踐過程,一種對於社會問題和生存體驗的認真的探索模式」(a risky experimental process and an earnest mode of engagement with social problems and lived experiences),而這種探索的動力和執著超越了好萊塢的視覺奇觀以及跨國媒體製造的幻象(fantasies)所營造的魔力(B. Wang 2009: 164)。
統整紀錄片的定義和課題,我們可以說「紀錄片是什麼?」這個問題經歷了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的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紀錄片往往被等同於事實,而忽略了紀錄片是一個帶有觀點的電影呈現模式。在第二個階段,「真實」或「虛構」成為紀錄片的主要問題,紀錄片的「虛構性」成為討論焦點。在第三個階段,紀錄倫理課題的浮現帶動了有關紀錄片「虛構性」的再一次反思,紀錄片與現實的連結重新被視為不可忽視的一環。紀錄片可以如此定義:紀錄片立基於與現實世界的某種連結,紀錄片是導演以現實世界作為材料,把素材加以篩選組織,表達某種觀點的現實世界的再現。但是,視拍攝目的之不同,影片可以凸顯「記錄」的功能,強調與現實世界的連結,也可以彰顯形式風格,以其作為一種導演個人的藝術創作。然而,無論紀錄片拍攝的目的和功能為何,「紀錄倫理」是所有紀錄片工作者共同遵守的規範,因為紀錄片以現實世界為基本素材,對於被攝錄入鏡的現實人、物,有不可迴避的責任。
本書章節結構安排
本書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章導論討論台灣新紀錄片的興起及發展歷程,在此章節,我們看到了台灣新紀錄片從1980年代中葉發展以來歷經的階段、開展的課題,以及美學形式的探索。我們從中描繪台灣新紀錄片的豐富面貌。但是,紀錄片在台灣,雖然歷經三十年的發展,研究方法依然是個問題。因此,本章節對於紀錄片的定義、研究方法和重要研究課題進行梳理。除此之外,也介紹紀錄片研究重要的工具書,方便有志於紀錄片研究的讀者後續研究參考。不過,紀錄片研究的這些理論只是基礎,不同主題的紀錄片解析,除了不同紀錄片理論之外,還涉及其他的批評方式。有如文學一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提供了女性文學和電影特殊的解析方法,而生態文學批評用來關照自然書寫或是環境電影,往往可開發出其他批評方式未及的思考層面。因此,導論提供的只是紀錄片的基礎理論概念和一些基本認知,各章節將視其主題進一步介紹各主題類型紀錄片可參考的研究方法,以發展深度的紀錄片論述。
第二章以「歷史敘述」為核心課題。1987年台灣解嚴,開啟了台灣歷史記憶和敘述的重整。1990年代可說是「重構台灣歷史敘述」的年代。我們在此章節透過五部台灣歷史紀錄片來展現歷史紀錄片對於歷史敘述和歷史研究方法上的貢獻,也探討歷史紀錄片的呈現方式和涉及的特殊課題。《跳舞時代》以「現代性敘述」呈現「摩登殖民地」來挑戰當時台灣歷史敘述的後殖民模式,李香秀的《消失的王國:拱樂社》(1999)探討「底層歷史如何可能?」而比令.亞布的《霧社.川中島》(2012)則展現了多重觀點的歷史敘述模式,也凸顯了挑戰漢人觀點的原住民觀點歷史敘述方式。這三部影片在歷史敘述方法上的開展,值得注意。這個章節有關紀錄片歷史敘述的研究,可說是我從1990年初步入學術生涯之後,對於「歷史敘述」研究的進一步延伸。1990年代台灣文學界最重要的一個課題便是「如何書寫台灣文學史?」,「敘述台灣」的深度探討,不能不深入探究「記憶」和「歷史敘述」的問題。年輕時的這些反覆思考成為本章歷史紀錄片研究最重要的理論基礎。本章節也藉兩部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製作、以台灣白色恐怖為主題的紀錄片(陳麗貴導演的《青春祭》與滕兆鏘導演的《白色見證》〔2002〕)來探討一個重要的問題:接受政府補助的歷史紀錄片的「獨立」空間在哪裡?
如果歷史紀錄片凸顯了紀錄片對於「時間」問題的探索,那麼,環境紀錄片堪稱紀錄片對於「空間」的投注。本書第三章即以台灣環境紀錄片為對象,以生態環境電影批評為方法,分析多部以「環境」為主題的台灣紀錄片,包括崔愫欣《貢寮,你好嗎?》(2004)、李道明《人民的聲音:環保篇》(1991)、紀文章《遮蔽的天空》(2010)、大暴龍《當怪手開進稻田中》、馬躍.比吼《天堂小孩》(1997)、《決戰時刻百萬青年站出來! 1/26 守夜行動!》、黃信堯《帶水雲》(2009)和沈可尚《噤聲三角》(2000),以及柯金源的《擺盪》(2010)。我們不僅看到了台灣環境紀錄片涉及的豐富課題,以及美學形式之多元,也深入探討美學形式與政治如何互相鑲嵌。最後,此章節討論一個特別的環境紀錄片類型―跨國
環境紀錄片(transnational ecodocumentary)來探討環境紀錄片的「在地性」如何開展跨地域、跨國、甚至全球的視野。
在透過歷史紀錄片和環境紀錄片這兩大類型討論紀錄片如何處理「時間」與「空間」的課題之後,本書第四章探討紀錄片作為一種有別於劇情片的電影獨特課題和研究重點:「紀錄倫理」。在紀錄片的領域裡,倫理議題之所以不容忽視,在於紀錄片所再現的是現實世界裡的人、事、物,紀錄片工作者不可迴避他們的作品對於現實世界和被拍攝者可能帶來的實際影響。如果紀錄片探索的一大課題是「真實」到底是什麼,那麼,紀錄片的另一大課題便是在這追求真實的過程中的倫理規範。紀錄片工作者追求真實的企圖必須受到倫理的規範。紀錄倫理可分為三個層次的責任:1. 紀錄片工作者對於被拍攝者的責任;2. 對於觀眾的責任;3. 對於他們自己的拍攝計畫的責任(J. Ruby 1988: 310; P. Aufderheide et al. 2009: 1; W. Sanders 2010: 544; P. Aufderheide 2012: 368)。紀錄片是否遵守這些紀錄倫理?當這三種責任有所衝突時,紀錄片工作者如何處理?這些是紀錄片研究的重要課題。本章節的討論涵蓋中國紀錄片《麥收》、楊力州的《水蜜桃阿嬤》、沈可尚的《築巢人》,但分析重點放在蕭美玲《雲的那端》、胡台麗《蘭嶼觀點》、張淑蘭(Si Manirei)《面對惡靈》(2001)和吳耀東《在高速公路上游泳》這四部反思紀錄倫理課題,彰顯紀錄倫理所帶來的挑戰的紀錄片。
最後,在本書第五章,我們把台灣新紀錄片的發展放置在亞洲新紀錄片的脈絡下來探討其意義和特色。與亞洲其他許多地方平行發展的新紀錄片相較,台灣的新紀錄片有什麼樣的獨特之處?作為像台灣這樣一個無論在政治或文化資本均缺乏國際能見度的國家的文化產品,企圖在國際影展場域裡被看見,所面臨的挑戰可能是什麼?受到影展評審青睞的台灣紀錄片是否有些共同的特質?這些特質透露了什麼樣的台灣紀錄片的優點和侷限訊息?台灣紀錄片如何開拓國際空間?本章節以山形影展獲獎的台灣紀錄片為主要考察對象來回應這些問題。此章節最後以賀照緹的《我愛高跟鞋》(2010)和簡毓群的《白海豚練習曲》(2013)來探討承襲台灣新紀錄片社會批判關懷傳統的紀錄片如何開拓國際發聲的可能空間。這個章節的討論以「國際發聲」為主題。這有個前提:國際發聲作為一種欲求,但是我們其實需先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台灣(和反映這台灣現實種種、創作風采種種的紀錄片)何需被看見?被認可?
不被看見又如何?
而如果被看見、被論述,但是沒有台灣觀點的論述,那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