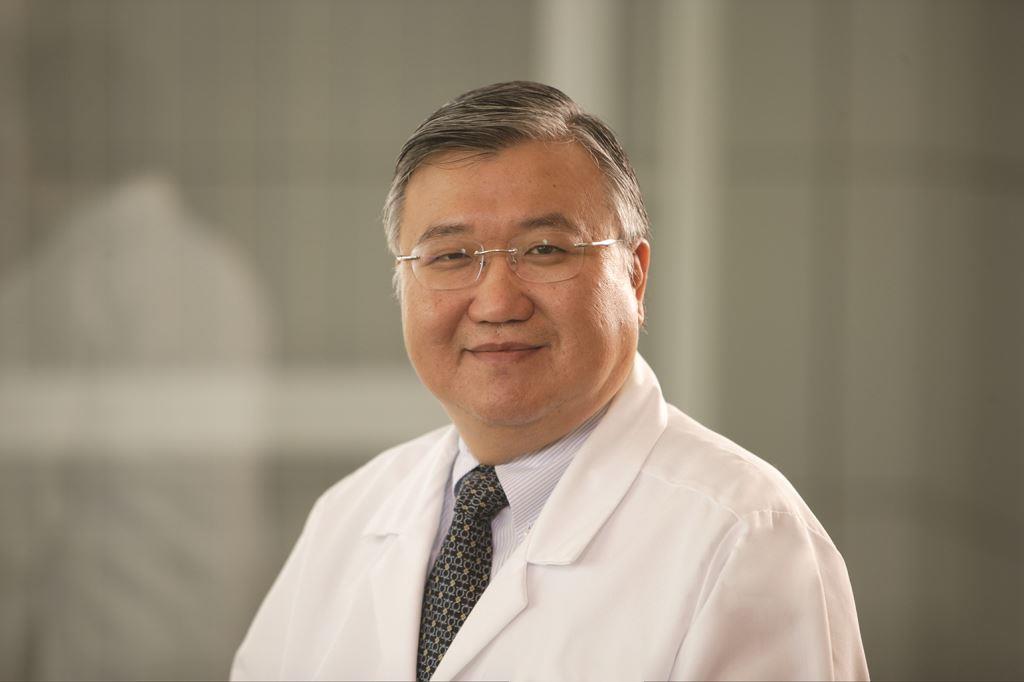眼看著女兒還有一年就戴方帽子了,這是她千盼萬盼的一天,站在醫師的立場,我也多麼希望自己能幫助上帝延長她的生命;問題是──老天總是與人作對……
這是一場非常辛苦且無奈的人生!從診斷出乳癌到去世,整整九年的時間,即使方媽媽一直努力地撐著,女兒也拼命地趕修學分,可速度就是無法與病魔並駕齊驅!
她開始生病時,女兒才上初中。而多年來小女孩手上帶著課本從代數、幾何、至 AP(Advance Placement,進階課程)課的物理,愈換,難度愈高,但陪著母親進出醫院的習慣,多年來如一日。
為了配合女兒上課時間,方媽媽的看病時間也總安排在下午女兒放學之後,母女倆一道來醫院,直至女兒升入大學後。女兒自然不願離開母親遠赴東岸唸書,但能獲得長春藤聯校之一的大學全額獎學金,是多麼不容易啊!母親也鼓勵她去。
小女孩在這樣的成長過程裡,已被訓練地非常堅強,學業與協助母親對抗疾病,幾乎佔據了她整個青少年歲月,沒空去交男朋友、去跳舞、看電影……,也沒什麼時髦的衣裳,永遠是樸實的牛仔褲。每每看到養尊處優的小孩,大聲地向父母要求這個、要求那個時,我都不禁會想到她。
她了解媽媽無法給她物質上的享受,也知道能讓母親欣慰的最大禮物是「一紙大學畢業證書」,然而病情每況愈下的母親能在生前了卻這樁心願嗎?她急切地想再多修一些學分,好提前畢業,可是一到暑假,她卻又必須回家陪母親,再一邊打工賺取下學年度的生活費,根本無法參加暑修。
棘手的治療方法
日子就在母女倆與時間的賽跑中流逝。一天,方媽媽打電話來醫院,說:「一隻眼睛突然看不見了。」我們立刻請她到急診室來,主要是右眼的視神經受到壓迫,神經科會診後認為不像眼底視神經直接受到壓迫,再經MRI掃瞄,發現她的視神經並非受到腫瘤的壓迫,而是腫瘤沿著腦膜往上走,產生一種浸潤(infiltration)的結果。
神經都是沿著腦膜進出,當腦膜受到腫瘤細胞侵襲時,它們會對神經產生一種浸潤,因此不會只是一個神經受到影響。果不其然,MRI做完之後,方媽媽已經變成不能說話了,這種非常戲劇性地單側眼睛失明,突然變成失語(aphasia),正是腫瘤造成的一種 leptomegitis carcinomatosis──腫瘤細胞侵入腦膜。
此種現象十分棘手,為了證明 MRI 的結果無誤,緊接著又進行脊椎髓取樣,第一次時並未發現癌細胞,由於錯誤率頗高,通常會要求做三次,第二次時確定有腫瘤,腦脊髓液內當然不應該有任何的腫瘤細胞。此時的她,已產生相當嚴重卻又不易處理的一種情況。
治療法十分複雜,無法使用普通的化學治療,原因是一般的化學藥物不能夠穿透腦血管屏障(blood brain barrier)。腦部是不能輕易受到藥物影響的,所以一般藥物打入體內,也不容易進入到腦,即是有腦血管屏障結構之故,以致藥物無法輕易過得去,抗癌藥物亦然,因此僅有少數幾種藥可以。
該如何治療呢?不能化學治療,不能放射治療,不能手術,只能打少數的化療藥物如MTX,打至腦脊髓內,不僅療效不理想,並且還要維持比較高的濃度。於是與病人討論一種特殊的方法,就是在腦殼的底下做一個小的手術,裝一個小水庫(reservoir),像一個鼓,拿掉頭骨,將藥從腦殼處直接注入,從鼓處逐漸滲入腦膜的血管系統裡。
這方法牽涉手術,牽涉治療,還牽涉到一個不是非常理想的結果,願不願意做?該不該做?……在在都是問題!
選擇放手不治療
女兒也從東岸回來了,初步的討論時,母親願意,畢竟她想要盡一切的方法來延長自己的生命,但女兒卻不贊同:「不要做了!」她了解百分比很低,延長的壽命時間一般僅有六個月左右,又何必再受罪?拖了這個病痛多年,女兒著實心疼母親身心所承受的罪!
做與不做之間,即產生了一個辯論,在進一步深談之後,方媽媽終於接受了事實:明白自己的預期生命已十分的短暫,做不做的差異實在不大。她改變初衷,接受了「不做」。
從醫療的角度,我們也認為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如果只是一個早期的病患,理當希望她能做手術,然而她已與癌奮戰多年,也有多處轉移,如果再做此手術,其實並不明智。
在她決定不做手術之後,兩週不到,腦壓開始增加,發高燒,旋即進入昏迷,幸好正值暑假期間,女兒可以一直陪在身旁,在平靜中,方媽媽漸漸地過去了。
人生,如何能盡如人意?但終究盡了力,也何來遺憾之有?母女連心,女兒一定也明白媽媽絕對不會願意未竟的心願,成為她心底一輩子的陰影──堅強如她,處理完畢母親的後事,即返回學校,繼續屬於她自己的學業目標,以及未來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