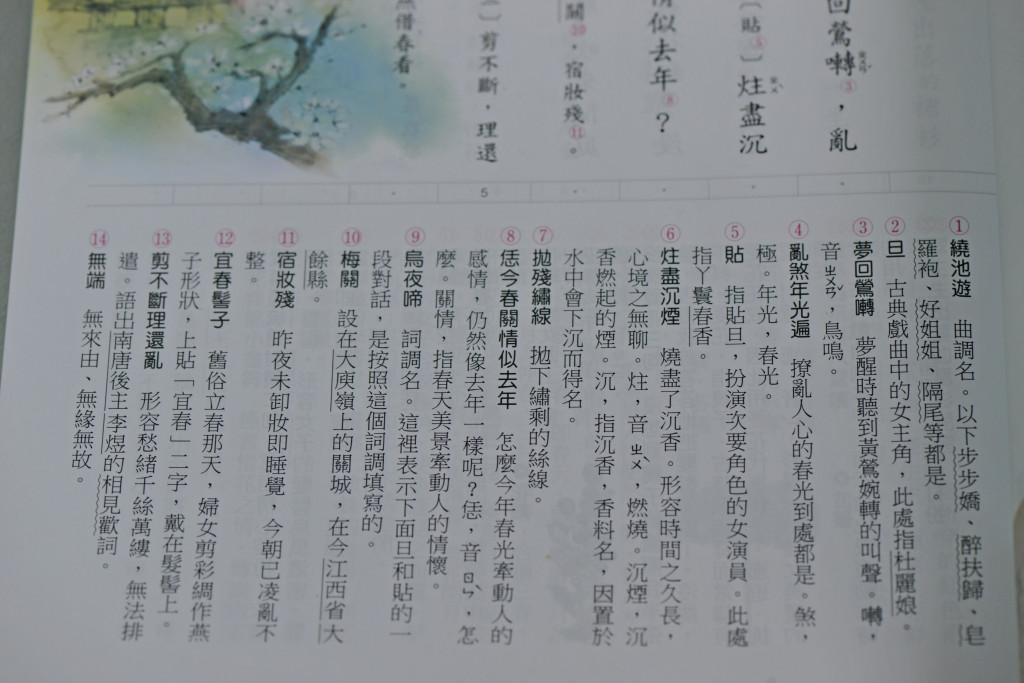李教授人文學養深厚,並不反對白話文,也主張推廣白話文,要六法全書白話文化,他也重現文言,他稱:白話,要從文言文汲取營養,這我也支持;而:文言文好,白話文才會好,只學白話會切斷了文體的傳承。大致的意思,類似的說法,我不知有無會錯意,不過很多文白並重者都這樣說,這是值得重新商榷。
漢字從漢代開始,大篆小篆到隸書、楷書,字形變化不大,可以說漢字已經傳承了 2000年了,白話文仍用漢字,並沒有特別奇怪。
同時間,由漢字綴合的文章,到20世紀初,這是我們通說的文言文,這是東亞漢字圈各民族的共通書面文章,這是漢字的優點,可以跨越時空。漢字、文言文是中國霸權擴張侵略的重要工具,這個問題暫不說,主要是因為古代漢語是孤立語,又沒有語尾的變化,而使漢字可以不必走向改為拼音字母之路,否則,東亞和歐洲一樣,會有數十數百個語族國家。
古漢語或者是中原的雅言,是統治者及其推動於统治圈的官方共同語言,不是庶民社會的語言。但這個共同語言因民族的混合不斷的變遷,元明之際有了現代漢語,就是入聲字消失,舌上音產生的北京官話。到清代,它也只流行於北方而已。
事實上,中國王朝所統治的民族、族群、語言或方言,太多太多,春秋戰國黃河流域,一國之內語言也要翻譯(見左傳),到20世紀中葉中國的語言,何止百計?上千種也沒有意外!福建一省語言大概就不下十種,往來根本就聽不懂,何況古代?
文言文從官方、從文人寫作流傳,完全脫離自己的實際語言,明末的所謂「唐宋八大家」,宋人偏多,多在長江流域的人,這是自然的發展,南方的語言複雜,三蘇四川人,還有江西人,不同地方的文人作家,語言不通,除非他們能通官話,他們共同能夠傳世的,就是與語言脱節的文言文。
總之,各王朝有通行的官話,但是統治階級所書寫的文言文,也不是官話,更不是與生活密切關聯的母語,母語有關身心、感情、感受和動作、行為的,最細緻、最體貼的語言、詞彙,豐富無比,這也是為什麼明清以後,白話小說逐漸興起的因素。
我們看紅樓夢,最傑出的是語言而不是當中的詩詞歌賦,這個白話是官話,還不是母語,當然母語還未必能夠表達人真正的情感思維「言不能盡意」的命題,這不是我們要討論的,要談的是,文言文簡短使文意不清晰不明確,用字晦澀,也使文意模寧兩可,它沒有辦法來詮釋深奧的學術論述,攸關人生問題的宗教與哲學的解說、推廣,必須突破。
文言文,盡量用口語來敍述說明,如唐代的變文,宋代佛教徒、理學家的語錄、語類等等,還有個人的記錄筆記,都可以看到白話的痕跡,文言文是帝國表面的包裝紙,裡面是各民族族群生活的語言文字,可惜,歷史大多只留下了華麗的包裝纸。50多年前,我買一本吳康「老莊哲學」老莊並論,我感興趣,可惜,大多是先引了大量的文本,再用文言文注評,我專心閱讀,卻不知所云。
當然,近代北京官話的白話文擴張,一定是一個地區被中原征服,語言被同化後,才能有北京話白話文的出現,今天,台灣在通行白話文,不是日本時代的台灣人所能夠想像的。
台灣有人說:主張白話文是去中國化,毫無知識,正好相反。
我大半輩子與古文為伍,古文的精簡,詞藻的優美,尤其韻文中詩詞,有的百讀不厭,我自知之。2、3百年白話文興起,尤其20世紀的白話文,早就吸取了古文的詞藻成語構句的形式,然而,異地異語產生的白話文未必要相同,受日本統治過的台灣白話文文學、東南亞的白話華文文學和中國有相當的歧異性,也不必然有中國古典文學的元素。
文言文和拉丁文一樣,老早就要退場了,文言古籍是研究中國古典文化文學的專業,是漢學,不是文學。現階段,我們主張不是完全不讀文言文,反對過去選文是忠孝節義的封建思想教條,仍保留為30%。
國文一課,應該改稱「語文」,是語言文學,就是活語言的文學,我們要訓練學生能欣賞多元的、包括外國的現代文學作品,用自己使用的語言來寫作,表達自己的思想意願,甚至可以創作文學作品。中國五四白話文運動,我手寫我口,使中國現代文學與國際合流,而有30年代一流的作家,一流的作品 。
同樣,台灣半世紀以來,湧現非常多傑出的小說家、詩人、散文家,他們之所以傑出,是在戒嚴苦難的日子中,他們的生活經驗融入了土地情感,這就是文學作品的本土化、現代化,也是語文教育的核心價值。
名作家鄭清文,台大商學系畢業,長期在華南銀行工作,他沒有讀文言文,年輕時就以小說聞名,他用字淺白,沒有中國古典的文風,20年前,他得到美國桐山太平洋文學獎,被認為是台灣可能得到諾貝爾獎文學獎的人選之一。
現代文學是建立於現代語文教育的基礎上,台灣這個北京官話的白話文,應該是經過70年的轉換,是屬於台灣本土化的北京話白話文。
文言與白話之爭,是不存在的,是因為當年蔣介石父子將國文課當作灌輸中國儒家倫理教條的工具,不是以語言文學作為教學目標,以致大量的放進古代的經典文言文,而混淆了語文教育的意義。
現在保留30%的文言文,應該是基於文學發展歷史的傳承,以及對本土早期古典文學的認識,而非是文言文比例的理由。
最後,宏觀的歷史。
台灣自古以來是南島民族的住地,500年前,如果台灣有文學作品那是屬於南島語族的白話文,荷蘭時代的新港文書就是西拉雅人的白話文,如果東寧鄭氏時代,建立了holo(河洛)文字,便會產生holo的白話文,而不必等到一百多年前,教會羅馬白話字的出現 。
北京官話的白話文與北京話文教育,居然是含有85% 南島民族血緣的台灣島民,全力打拼要爭取的,這是歷史的偶然嗎?若是台灣人猶停留在使用文言文的時代,那是不是意味著,台灣各族的語言仍然存在,而迥異於北京話呢?
可悲的台灣人,他們不是在爭取同於中原古漢語的HO客語文的復活,和主體性、主導權,而是在爭取受遊牧民族影響的所謂北京官話語文,這是歷史的吊詭與諷刺。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