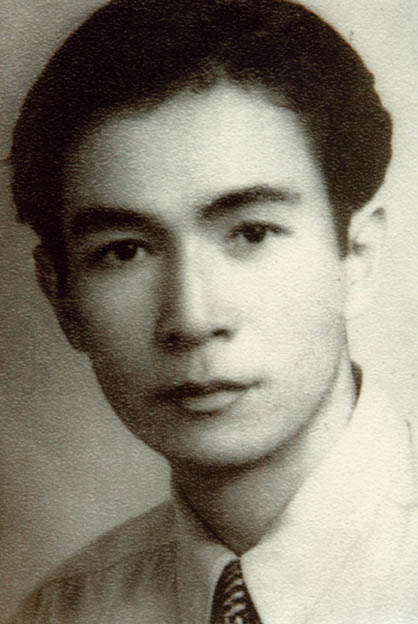鹿窟故事並未結束,它是台灣前途的預言
今年是鹿窟事件六十六周年。在白色恐怖研究上,鹿窟事件是一個極具指標性的案子,不只因為它是本省案系列的第一大案(僅次於外省系列的海軍案),更因為它是整個白色恐怖的縮影,白色恐怖許多基本要素如驚悚、殘酷、出賣、背叛、刑求、槍決、囚禁、逃亡、革命倫理的蕩然、謊言詐騙的泛濫、泯滅人性的加害、慘絕人寰的受難等等,在鹿窟案應有盡有。很難想見,這個在地圖上不起眼的貧窮山村,竟上演白色恐怖最驚心動魄的情節。換在國外,鹿窟案早就拍成史詩型的電影,橫掃國際各大影展;而在台灣,很多人(包括近在咫尺的天龍國國民)對鹿窟案仍聞所未聞,遑論了解。
緣起:從一群大咖上山活動開始
要了解鹿窟案也不難,至少案情脈絡並不複雜:二二八事件之後,一群「省工委」台北市工委會的大咖們(其中有許多是工作委員、支部委員、支部書記級的幹部,村民不詳其來歷,一律稱為走山仔)在1948年前往鹿窟活動。他們透過陳春慶(鹿窟的出外人)的引介,認識村長陳啟旺;再透過陳啟旺父子的關係人脈,建立在地的影響力;然後施展各種話術和手段,軟硬兼施,半鼓勵半恐嚇,吸收許多根本不知共產黨為何物的村民,加入他們的紅色團隊(號稱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或作工役,或充跑腿,或當眼線,鹿窟基地於焉建立。
及至1952年冬,當時「匪諜」已被捕殺殆盡,專辦匪諜案的保密局生意日漸清淡。不巧,兩個「走山仔」曝光,一是溫萬金記載在鹿窟受訓的日記被當局查獲,二是汪枝被捕自新,「對匪鹿窟基地情形,供述甚詳」。這些線索不啻為保密局打了強心針,乃於當年12月以剿滅武裝基地為由,由偵防組長谷正文指揮上萬名軍隊大舉封山,前後逮捕及偵訊896人,鹿窟家家戶戶,幾乎無一倖免。
從官方檔案可知,在眾多白色恐怖案件中,鹿窟案的「叛亂」程度只是一般般;唯一被允許加入共黨的在地人只有陳田其(其他人只准加入外圍組織,即上述「保衛隊」),和基隆案、台北案、學委案整個陣勢排開幾乎都是黨員相比,根本是小兒科;至於「武裝」兩字更談不上,雖有幾枝槍,純供幹部防身自衛,毫無戰鬥能力。若放在1950或1951年,鹿窟案頂多像台中一些不是武裝基地的武裝基地案,殺幾個人關幾個人結案。
不幸的是,由於蔡孝乾(省工委領導人)和「走山仔」對鹿窟基地亂畫大餅(包括建立「山地解放區」和進行「小型兩萬五千里長征」,全屬紙上談兵,且鹿窟人並不知情),加上基地存續四年,牽連者眾;以及「匪諜」奇貨可居,供不應求,特務乃將本案大作特作,極盡羅織能事,導致本案有93人被判刑(其中28人死刑),1人被當場擊斃,19人被谷正文長期非法驅役,充當奴才與下女,這還不包括被刑求和被搜刮財物的人數。甚至當地的信仰中心:鹿窟菜廟,住持也遭軟禁,佛堂淪為刑求場,清淨莊嚴的暮鼓晨鐘,變成鬼哭神號的阿鼻地獄。經此「滅村」悲劇,鹿窟人長期無法翻身;坐牢回來的男人,為求溫飽只得入礦坑,由此展開另一段「矽肺人生」。
教訓:革命是一場兒戲一場夢
對後人而言,這麼悲慘的大案一定有一個慘重的歷史教訓,而這教訓絕不是罵罵國民黨、唏噓鹿窟村而已。鹿窟案(和它所衍生的其他案子,如大同鐵工廠案、綠幫革命團案等,以及部分人士供出逃亡期間藏匿哪些人家,由此又牽連一些人入獄的案子)最值得後人省思的,是革命倫理的問題。鹿窟的走山仔(陳本江、陳通和、汪枝、李上甲、盧哲德等)以及穿針引線的陳春慶,因為向當局「交人」(供出同案或其他案的人),最後全身而退;反而是被他們吸收、欺騙、利用的群眾紛罹其殃。這些「交人者」有的是高學歷,講革命、談理想頭頭是道,然而時窮節乃見,等到大難臨頭,也顧不得共產黨的招牌了,紛紛拋棄群眾,保命自首。
宏觀來看,不只鹿窟案,1950年代的政治案件,此例不勝枚舉。從蔡孝乾以下,許多共產黨員也是滿懷社會主義理想,要學歷有學歷,要口才有口才,也會用各種話術拉人,等到猝然應變,也把革命倫理丟了。為了換取活命機會,很多人寧願「死道友不死貧道」,出賣他們的同志、群眾甚至恩人。固然形勢凶險無比,而且誰不惜命,一味怪他們「貪生怕死」有失厚道;但歷史是拉長時間來看的,革命倫理的承擔不是死了就算了。一直到現在,除了很少數的例外,我們看不到這些「革命者」對被他們犧牲的人及其家屬的懺悔、救濟與贖罪,這無異宣告革命信用的徹底破產。
隱喻:鹿窟預言台灣的現狀與未來
凝視這段歷史,革命的真相竟是如此不堪。革命是這樣搞的嗎?背棄同志和群眾,不負責、不善後,豈非鬧劇一場?歷史的諷刺不只如此。同樣的情形,把「革命」換成「改革」,放在今天的台灣,完全無縫接軌。許多號稱「改革者」也是要學歷有學歷,要口才有口才,也是選前滿口承諾,選後擺爛敷衍,改革不做,弊案不查,背信心態與革命者無異。不幸的是,台灣因為特殊的歷史命運,對「困局解決者」和「前途引導者」的需求甚殷,這就給了騙徒可趁之機,戰後至今七十多年,我們被共產黨騙了,被國民黨騙了,被革命者騙了,也被改革者騙了——台灣福薄,像李登輝這樣的大改革者絕無僅有。從這個角度來看,「鹿窟案」不僅是一個事件,更是一個隱喻,一則預言,和一個封印台灣前途的魔咒。
話說回來,把過錯全往騙徒身上推,也不盡然正確。以當下而言,政客儘管習於詐騙,卻沒有一手遮天,他們露餡露得如此嚴重,已經昭告其不可信任,但愚痴的粉絲、死忠的支持者仍為他們硬拗硬辯,讓他們騙得更加安心。這使得民主最重要的監督機制失靈:獨裁者可以長享政權,詐騙者也是。台灣的詐騙文化舉世聞名,不是沒有道理。直探核心,那是台灣人的品質問題。這個民族若沒有徹底自省,任憑再多的歷史殷鑑,還是走不出困局與騙局。
典範:革命黨做不到的,他們做到了
然而,1950年代的革命運動果真是一文不值嗎?不然。革命黨人雖然背叛革命成風,但也有寧死不屈、守口如瓶者。他們與特務精心鬥智,把一切責任攬在身上,盡量避免牽連別人。說真的,這難度極高,但他們盡了最大努力,捨己救人,堪為典範。只是這樣的人格者在革命黨究竟有多少,是一個謎;而且,他們不一定是白色恐怖研究聚焦最多的「明星」。「明星」不一定能在最後關頭全其志節,有時這跟機運有關。例如人稱「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原是鹿窟基地領導人之一,與陳本江知交。但呂赫若在基地被破獲前死於蛇吻,得以避免成為另一個陳本江。
台灣的白色恐怖研究,長期以來都在「明星」中找「典範」,但隨著檔案越來越開放,有些「明星」會越來越禁不起「典範」的檢驗。而白恐研究又不能沒有典範,否則這段歷史會淪為徹底的荒蕪與絕望,沒有教育意義可言。其實典範並不難找,只要去除「明星」的迷思即可發現。從革命角度來看,鹿窟案最大的污點是出賣與背叛,那麼它的典範就是不出賣與不背叛。
就現有的口述史與回憶錄來看,至少有四個人堪稱典範:蕭塗基、王新發、李石城、陳政子。礦工蕭塗基(1912-1955)叮囑李石城:「我們都要覺悟,我們這些人是穩死的。但無論如何被打,也不要供出別人。你一定要記得:人總要死一次,抱著必死的決心,還有什麼可怕的呢?」農民王新發(1929-1955)面對特務,則始終一問三不知。他們兩人都受同樣的刑求:綁在長條凳上,全身赤裸面朝地,被特務用粗繩狠命抽打。蕭塗基血流不停,仍咬緊牙關,不哼不叫不求饒;王新發一打就是一小時,打完後,特務還在他的傷口淋酒。他全身發抖不停,臉色蒼白,卻絕不哀號。這兩人涉案較深,最後都被判死刑,但走得一身清白。比起省工委的許多幹部,他們更像真正的革命黨人。
李石城(1935~)當時是牧牛童,雖僅17歲,但已是小組長,這足以送他到馬場町。幸好蕭塗基的一番話,使他有了心理準備,對特務的一切指控一概否認到底。他在回憶錄《鹿窟風雲》詳述親歷的「無止盡苦刑」,包括石磨壓身、綁拇指吊刑、盪鞦韆吊刑、頭下腳上吊刑、老虎凳(李說其痛如「萬蛇啃咬」)、摜頭浸水(使其體驗溺死滋味,李說他臨死前拚命掙扎,特務卻快樂無比)、「竹橋渡仙」(沿自清朝酷刑,李石城說「受此酷虐,人已半死」)、鋼針刺指(沿自漢代針刑,李說痛得椎心刺骨,屎尿失禁)、水沖鼻孔(李說腦內像萬蛇滾動,呼吸極度困難)等。這種種「求生不得」的刑求,使他一度撞柱自殺,然而「求死不能」,仍被急救回來,繼續受刑。不過再怎麼痛苦,他始終守口如瓶,最後沒牽連別人,也保住自己,判刑10年,如今成為鹿窟案最重要的見證人之一。
傳奇:12歲小女孩的絕境反抗
和上述三人相比,陳政子(1940~)的典範意義更加凸顯:一者,前三人都是成年或將成年的男性,陳政子卻是一個12歲小女孩;二者,前三人都有參加組織,她沒有,只是一個知情者和跑腿者;三者,由於她是村長的女兒,得地緣和人緣之便,特務要她供出比前三人所知道的更多的線索,也就是說,要她出賣更多人:四者,由於她沒參加組織,比較事不干己,理論上似乎更容易供出別人。雖然如此,這個小學生卻能忍受種種酷刑,絕不鬆口;而且與特務鬥智,展現超齡的沉著應變,最後完成「零供出」、「零指認」的自我要求,並贏得鹿窟人的尊敬。特別是,她不懂什麼革命理論,一心只想保護村民,和那些夸談革命理論,最後犧牲別人以求自保者,恰成強烈的對比。
這種近乎傳奇的「鹿窟女兒」故事,晚近(2015)在中研院台史所學者許雪姬主編的《獄外之囚》下冊〈陳政子訪問紀錄〉中,第一次有完整的披露。台大教授陳翠蓮的訪問功力一流,使該文具有極高的可讀性;又因為它是筆者所見白色恐怖口述史中,最深入細膩的作品之一,因此基本上具備將故事轉化為教材、繪本、小說、戲劇所需要的各種元素,特別是心理層次的豐富細節。她的故事,是歐美人權電影、政治驚悚片求之不得的題材,而在台灣,我們才剛發掘出土,並且把它晾在一邊。
主導對陳政子刑求的人,是保密局大特務莊西(莊稼農),他命令這個小女孩兩手伸直,任由國軍毒打,打到竹棍裂開,而她的兩手也失去知覺後,又命她趴在木箱上,繼續朝屁股狠打。陳政子全身痛楚,「比死還要慘」,仍嚴密口風。莊西見她不招,又拿藤條朝她大腿抽打,並威嚇「我每五分鐘就會打她一次,看她何時會老實招供!」她回憶當時的心境是:「死就死吧,死了就更不用怕他們了。」經此刑求,她已傷痛不堪,且無法進食,吃飯變成苦差事。但特務仍不罷休,繼續讓她飽嚐各種心理威脅。
陳政子不僅有驚人的忍耐力,還有同齡孩子少有的機智。她幾乎能讀透特務所有話術背後的陷阱,而迂迴繞過,或以計拆計。例如特務抓了許多人要她指認,身為村長的女兒,不能說都沒看過,就回答「看過,但不認識」,看過是符合常情,不認識是保護雙方。又特務逼問她哪裡有草寮(走山仔匿居之地),她不能說都不知道,於是就帶他們到各處專門燒木炭的炭窯工寮,讓特務去搜索,跑來跑去白費力氣。
特務又施一計,要她在齋堂對佛像發誓,保證絕無知情不報,否則晚上會被魔鬼抓走。村民畏神,兒童怕鬼,此計雙管齊下,堪稱絕招。陳政子的因應之道,就是嘴巴跟著特務唸誓詞,心裡卻默求:「釋迦牟尼佛、觀音佛祖,這不是我願意發的誓,是他們逼迫的。他們這些壞人對我如此殘暴,讓魔鬼去抓他們這些國軍好了!」神明不會為不義背書,宗教不是罪犯的遮羞布,這個小女孩比時下許多高級知識分子還要懂。那些玩文字遊戲的政客(教唆犯罪,把責任推給屬下,再發誓「自己」絕對沒有舞弊收賄云云)、褻瀆宗教的法官(宣稱惡行重大的殺人犯,因為抄抄佛經,「有教化可能」,判決免死,再把責任推給「兩公約」去背黑鍋),其良心愧對神明,其判斷不如小學生。
人權:保衛家園反抗侵略,相救不要相害
陳政子的故事極具戲劇張力,本文限於篇幅,只能幾筆帶過。她的無畏承擔,最後救了很多鹿窟人,避免更多犧牲。事實上,革命的初衷是救人(而非殺人),從這個角度看,這個小女孩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但她又不是革命者,她只是一個堅持道德良心底線,單純想要保護村民的小女孩。她的典範價值就是「道德良心」四個字,這是我們研究白色恐怖歷史,千迴百折尋尋覓覓之後,所獲得最珍貴也最簡單的啟示。
台灣人可以自傲的是,白色恐怖史最少有六、七百人甘冒生命危險,因拒絕出賣(官方稱為知匪不報)或救援危難(官方稱為藏匿叛徒)而被定罪,也就是最少有六、七百個典範存留青史。從國民黨觀點來看,他們都是叛徒的「幫凶」;然而從台灣人觀點來看,真正的凶手是國民黨,因而拒絕配合國民黨行凶的人,不可能是幫凶,只可能是英雄和典範。
從人權觀點來看,陳政子的故事也發人深省。長期以來台灣的人權論述,都聚焦在「國家暴力」與「人民」的互動上(前者壓迫後者,或後者反抗前者),較少觸及「人民」與「人民」的互動(相害與相救),這點台灣落後歐洲國家一大截。更宏觀來看,正如鹿窟案的出賣村民是台灣歷史的隱喻,陳政子和前述三名男性的保護村民也是。台灣不斷被外來政權壓迫,也不斷有人為了保護家園、反抗壓迫而奮鬥——他們戰前反抗日本,戰後反抗國民黨,未來萬一中共侵台,也必然反抗中共——當然在反抗的同時,千萬記取教訓:不要出賣別人,也不要被別人出賣。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