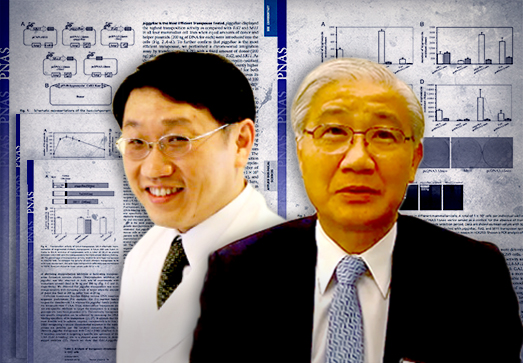【編按】 PubPeer 這個出版後同儕審閱的網站,是臺灣這波學術造假案的初始戰場。臺灣從來沒有像PubPeer 這樣可以不受官方干擾、不受大學閥左右的學術揭弊場所(儘管揭弊可能不是PubPeer成立的本意),因此五個月以來,這個網站就成了臺灣學術界的熱鬧推理劇場。在網頁上各式各樣不同的爆料中,雖然有些是可以輕易回覆解決的烏龍指控,但更多的詰問則是需要嚴肅面對的錯誤 ------ 不管是可以原諒的無心誤失,或是蓄意為之的造假。
但很遺憾的,目前我們看到在此波案件中主要被調查的諸人,面對他們被指控造假的論文(包含那些宣稱已完成勘誤程序的文章),沒有一位願意真誠的向學術界、向大眾說明造假原委;覺得受冤枉的,也未見主動以原始數據或是重現其實驗的方式,公開其勘誤的過程來證明他們的清白。致使這段期間內,人們對臺灣學術界的印象只剩下各級當事人的狡辯避責,毫無擔當的學術沉淪;而受害最大的,不是那些造假的徒眾,而是眾多兢兢業業、謹守科學本分的研究工作者。
還好,我們看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例子。
受訪者是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的楊慕華教授,他在此次的風暴中,因為有些已發表論文的作者群中列有台大造假案的某些主角,所以也被科技部列為調查對象。在他被調查的論文中,有些的確有缺失,勘誤了,有些則是別人蓄意挑剔,僅需澄清說明。我們詢問了楊教授的意願,他非常樂意公開他所有與期刊交涉勘誤過程中的資料,也願意公開他被指控有問題的圖表之原始實驗數據,亦同意公開在原始數據外,為昭公信所重做的實驗結果。也因此,《科學月刊》決定進行這次訪談。
在呈現訪問內容之前,請容我們先將受訪者的感言在此寫出。
「我一定要努力,我要告訴人家不是臺灣做生醫的都是假的。我要好好的做,要告訴人家我們可以做得很好、也嚴謹。人都會有疏失的時候,但出現了疏失我會面對,我會盡我自己所有的力量,以證據去告訴人家說我這個地方已經澄清了。我要告訴人家,我們正正當當的做也可以投到頂尖的期刊,而且我不是為了追求高影響因子,而是要告訴人家我們臺灣的生醫對於世界上的生物醫學研究是可以做出真正的貢獻。」
希望您讀完全文,也繼續鼓勵真誠的研究工作者。
【訪談記錄】
科月總編輯(以下簡稱「科」):這次你的文章有些還是有勘誤。你認為什麼狀況是可以勘誤的、什麼樣的狀況是造假?如果讓你來審查,你會用什麼樣的標準來看待勘誤與造假的分別?
楊慕華教授(以下簡稱「楊」):勘誤其實在各期刊的每一期幾乎都會有。如果這個勘誤不是拿另外的數據來使用、也不是刻意的變造的話,我覺得這樣的勘誤是科學界允許的事情。
科:不過這次的狀況是有些論文雖然已經勘誤了,但是不管是臺大、科技部或教育部的調查都認為是造假。我想問的是,如果作者被指控造假,但期刊已接受勘誤了,那得要看到什麼樣的證據才能判斷是非刻意變造的無心之過?
楊:第一我會看他提供的資料,看他有沒有辦法提供他當時的原始資料,這是最主要的;第二個是他這個東西是否是重複使用別處的資料,但是否是蓄意重複使用,有時候真的很難去判斷;第三是數量,如果文章裡只有一處,或許真的只需勘誤,但如果一篇文章裡有十個,那就不是勘誤可以說得過去的了。
不過,這種判斷的過程像是法官在定一個人有沒有犯罪,是要先推定這個人有罪、還是先推他沒罪,這個心證空間蠻大的。
科:但若作者辯解說因為2006年距今已超過十年了,可能筆記本丟掉了、電腦硬碟壞掉了而找不到原始資料,那你會要求什麼樣的查證程序?
楊:我會希望他跟期刊勘誤的來往信件讓我知道,看看他對於那些有問題的東西解釋是什麼;若如果可以的話,他是不是應該要重複他的實驗。今天這個事件,我覺得給臺灣的科研非常好的教訓,不管之後所投稿的期刊是否有要求,我們都應該完備我們對原始資料的保存。不過還是剛剛所提過的法官判案,PubPeer上在質疑文章跟期刊審稿人看文章不同,PubPeer覺得這可疑,覺得你這個lane很像就是很像,作者就必須得提出反駁;但反駁了你還是覺得很像,作者就得要再不停地提出反駁。這個假設的起始點是有罪認定,因此若以有罪認定出發,那是不是所有人受質疑時,都應該把自己所有論文的原始數據都上傳?但所謂的原始數據要保留到什麼程度,保留幾年?
科:這裡就衍生出另一個問題。這陣子PubPeer上有很多烏賊戰,一堆論文都被找碴。對於論文被放上去公開質疑,你覺得最好的應對方式是什麼?
楊:作者不能閃躲,必須要回應,但是回應了,人家不一定會滿意。像我自己的論文被質疑時,在那個時候的氛圍很難說是不是善意,很多人跟我說不要再回應了,可是我就是堅持。第一時間回應的時候,需要找到原始資料,雖然有時後原始資料不見得找得到,可是我會盡力的去找,盡我所能的去找,所有的電腦調出來找,所有的記錄本翻出來找。
雖然我還是有一個找不到,但是我有個佐證的方法,因為只要我當通訊作者的論文,一定都是我自己完成線上投稿程序的,不會假手他人。因為那個問題很像是投稿過程常見的壓縮成PDF檔時之失真,亦即原始上傳檔案是用JPEG或是TIF那種解析度很高的格式,但在PDF壓縮過程就會遺失些細節。所以我就用當時上傳時的原始資料,這個資料我覺得是有公信力的,因為如果說調查有需要,我可以當場開給你看,那是我無法去竄改的歷史記錄。
所以當時我在兩天內找到原始資料回答質疑。當然有些質疑沒道理,我曾經被質疑這兩個柱狀圖的柱子一樣高,但其實拉條線就知道兩個是不一樣高的,這就很簡單的回應即可。不過有些質疑是真的論文出現錯誤,那我自己就得認真追究錯誤是怎麼發生的。譬如說我做了六組,有一組放錯了,那就得回去那個組的原始資料裡面找,確認那只是真的把圖片放錯而已,接下來就得盡快寫信給期刊勘誤,然後把勘誤來往的信件留著。
但這樣還不能算結束,我覺得今天做為一個負責任的科學工作者,不能只是勘誤就了事!你必須要重複你的實驗,告訴人家說,這個實驗有錯誤但是我可以重複!像我被質疑的東西,雖然大部分都沒有錯,可是我就是重做,重複了3次!所以我的實驗室有幾個月都沒有任何新的進度,全力把所有被質疑的地方的實驗都重複3次!
科:你到現在總共勘誤了幾篇論文?
楊:2篇。
科:你願意把勘誤的過程直接公開嗎?
楊:願意。[註1]
科:包括你重新重複的實驗數據?
楊:是的。[註4]
科:另一個問題是責任歸屬。即便是第一作者,但是沒做文章中那個出問題的實驗,那要不要為此篇論文的造假處負責?你怎麼看待各作者該負的責任?
楊:就第一作者來說,我覺得要看第一作者跟通訊作者之間的關係。如果第一作者是通訊作者的學生,那我覺得通訊作者要負主要責任;如果第一作者跟通訊作者是合作者的關係,那這個時候的各作者都得分攤責任。但第一時間該出來道歉的,一定是通訊作者。
至於各作者的責任要如何區分?若說不是通訊作者也不是第一作者,你只是一個列名在中間位置的學生,而且所負責的數據也沒有被質疑,那我覺得應該是沒事。但如果是一個計畫主持人,而且你的貢獻是含糊(ambiguous)的,你就得澄清你做了什麼。若是他負責的部分之外的其他地方造假,那我覺得他基本上不用負責,但是仍必須有榮辱共擔的義務,因為投稿前,通訊作者應該會把投稿資料給每個作者看過才能夠投稿,因此論文若有問題,他還是必須要承擔部份責任,只是責任輕重與通訊作者有很大的差別。當然,但如果說他的貢獻含糊到難以清楚確認,這時的責任歸屬就需要更多方考量了。
科:現在很難有單一作者的論文,特別是生醫類的論文作者常常一大堆。經過這次事件後,對於一篇有多位作者的論文,你將以什麼樣的程序來檢查各作者的誠實度?
楊:這可能有兩種情況,一個是他就是幫忙收集樣本,或者是提供試劑,這時所有的數據還是在我的掌控之下,那就沒問題。那如果說他做的是我不會做的實驗,他完全負責那部分的數據,我現在可能就會要求所有的原始數據要給我;同樣的,若是我協助其他人的論文,我也會把原始數據給他,讓他自己也保有我負責的原始數據。
科:如果對方不給你原始數據呢?
楊:那就不要投稿。
科:所以合作對象是重要的。談談你是怎麼找合作的對象?
楊:主要是各種開會的場合,譬如說各種的審查委員會、學生的論文委員會或者是學術研討會議,會很容易知道什麼東西是誰會做,如果說有需要的話,就可以主動去跟人家聯絡。
科:你有特別考慮他們的信用或是其他的紀錄嗎?會先評估一下這些,再去找合作對象?
楊:會,但將來會更仔細,變成首要考量。我覺得這次事件的經驗,算是突然在臺灣生醫界訂了一個新的遊戲規則,對於年輕一代的人來說這也不錯,以後都有一個好的規則可遵循,之前是這個規則不太清楚,但是現在很清楚,就是以後大家合作的時候,到底該考量那些事情,就像前面提到的,一定得願意提供原始數據。
科:你這次會被調查,其實最主要是因為你有論文跟張正琪同列作者,那是導火線。方便談一下為什麼你會找張正琪合作嗎?
楊:其實很簡單,因為我是做口腔癌的,臺灣做口腔癌基礎研究的人真的不多,在2006還2007年的一個亞太口腔腫瘤學會,我就認識臺大做口腔癌的幾位老師,不只她,還有其他人。因為年紀上算是同一輩的,溝通上比較容易沒有輩份上的問題,所以就有了些合作的提議。
科:她有什麼樣的技術是你自己沒辦法做到的,所以要找她合作?
楊:倒是沒有,沒有特別的技術是我不會的,但因為2007年那時候,我剛有實驗室,非常小,她那時也是剛有實驗室,但比我大一點,資源比較豐富一點,那個時候有一點算是合作實驗室,有她的學生來我這邊做,但我沒有學生去她那邊,因為她的學生比較多,我的學生一開始很少,所以就是她的學生在我這邊訓練,也做合作的題目。
科:教育部、科技部都有調查你的論文嗎?
楊:教育部沒有。
科:方便談一下科技部的調查程序嗎?
楊:科技部就是寫個信給我,說有人檢舉我,檢舉了我哪幾篇。其實,就是很簡單的照PubPeer上指控我的,從第一條列到最後一條。
科:總共有幾篇?
楊:4篇,都是跟張正琪老師共同發表的論文。或許科技部就是以張老師的著作為主,跟她一起列共同作者的都調查。
科:只是書面要求提供說明嗎?
楊:對,書面提供說明。
科:有沒有要你去現場報告?
楊:沒有。
科:您提供了書面說明之後,科技部有回應你什麼嗎?
楊:沒有。
科:也沒有跟你說沒問題?
楊:沒有。我後來有主動查詢,科技部是說初審如果沒問題就不會再通知你,如果有問題的話,複審才會請你當面再解釋。
科:您回覆科技部的時候,你有跟論文的其他作者聯繫說要怎麼回覆嗎?
楊:有啊,我要求相關實驗的人要把原始數據找出來。就像在回覆PubPeer的質疑那樣,馬上回應,然後把原始數據全部貼出來,那告訴質疑者哪一些是他看錯的,哪一些是我有錯的。我有錯的就勘誤,但我可以把我勘誤的來回信件都給你看。再來是我重做3次的實驗結果也都貼給你看,我就是以這樣的程序處理每一篇。
科:您方便把回覆科技部的內容也全部公開?
楊:可以。[註2、註3]
科:教育部沒有調查你嗎?
楊:沒有。
科:臺大也沒有要求你幫忙什麼?
楊:臺大只有因為一篇與張老師共同作者的論文,要我書面回覆我的貢獻度。
科:榮總或陽明有沒有調查你?
楊:陽明有問,我也做了解釋,校方有接受我的說明。
科:陽明是什麼單位詢問你?
楊:人事室跟教務處,因為臺大的公文是去到那邊。
科:有了此次的經驗,您將來要怎麼去預防實驗室發生這類錯誤?
楊:其實我最近還是一直在投稿論文。就我自己的實驗室來講,很簡單,就是把A的論文請B看,我就請B當作是PubPeer,就找碴,學生之間互相找碴,特別是關於圖表的內容,然後B看了之後再叫C也做一次一樣的事情。有時候真的會找到圖有擺錯的。另外就是每一次的實驗進度報告時盯好數據的整理,不只要報告原始數據,連實驗時的各種條件都要寫好,像是在什麼溫度下做的。還有檔案保存也是重要的工作。我覺得這次事件對大家的教訓是很大的,將來要盡量避免疏忽造成的錯誤。
科:要投稿期刊的論文都是你自己寫的,還是學生寫完你修改?
楊:學生寫完我改,但一定是我來完成投稿程序,我不會給學生按最後那個送出的按鍵。學生的初稿其實常常變成我要改寫(rewrite),畢竟我在正式發表上還是比較有經驗。文章中需要的圖表該如何呈現,我會跟學生一直來回討論,所以每篇論文我都還是花了非常大的力氣在做這些事情。
有的時候人會卡在論文的繁雜內容中,這時候請一個他對這篇論文內容沒多少了解的人,只就圖表的呈現與出現的邏輯檢查,我覺得還蠻有幫助的。他可能在幾個小時的時間內,看出某兩個圖很像,這時候,做實驗的人就把他的原始數據給他看,讓他判斷有沒有貼錯。如果說還是覺得可疑,就再找一個有經驗的人來判讀確定。我現在是用這樣的方式來預防,但能預防到什麼程度不知道,就是盡力。我們當老師的人,一定要把持住最後一個關卡,在投稿前要一再的確認,所以我才會堅持通訊作者的那個送出按鍵一定要自己來按。
科:事前預防重要,事後懲處也可以有阻嚇的效果,但目前大家普遍對於檯面上看到的懲處都覺得太輕。什麼樣的懲處,您覺得才是合理的?
楊:這得在法律條文裡面寫清楚,不管是否要追回全部的經費,總要有法律的依據。雖然今天發生不對的事情,可是在發生這個事情之時並沒有明確規則可依循處理,所有問題就可能會被一直上綱,變成問題不論大小,皆要最嚴厲處置。我覺得因為這次事件而有機會在臺灣樹立一個處理的標竿,以此建立新的共識與規矩,像是勘誤要不要處罰、調查要不要回溯、經費要不要追回等,都需要有明確的規矩來處理。
科:關於這整個事件,您還有沒有想說的感想?
楊:我的感想可能會跟大家有點不一樣。其實我算是受害人,這段時期某個程度社會上是陷入一個獵巫的狀態,今天在PubPeer被找到的人就是巫,要被獵掉。我在那個時候心情非常低落,雖然我覺得說我做事很小心、很認真,那可是後來還是被找到缺點。其實很多人都有被找到,包括在媒體上發言的一些意見領袖的人也有被找到,就算是某些參與連署的人也是有被找到!
(編按:陳培哲的問題論文,《科學月刊》在報導中提到了幾次,他也有因為PubPeer指控而勘誤的文章,但並沒有主動跟大眾說明。)
楊:這就是很弔詭的地方。不過我覺得科技部講得很對,今天用公權力介入時,必須要很謹慎的使用公權力,不能隨便就處罰一個人;當然,也不能不用公權力去解決事情。但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太負面了,負面的能量非常非常大,我有段時間非常非常的沮喪,常常會想說我當醫生就好了,今天做這些研究又不是會有比較多的收入,根本沒有;也沒有比較有名,或許學術界裡有些人知道我,但在醫學界裡很多人就不太認識我。我對這類的名氣也不是很在意,那是不是就乾脆不要做研究,就只當醫生就好了?
可是後來是因為我必須對我的學生負責,另一方面還是覺得割捨不下我對研究工作的熱情,所以差不多在沮喪了一個月後,我覺得還是應該回來面對,然後才會想出那幾個層次的回應,包括以原始資料勘誤、重複驗證實驗等。我想到我能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這些,但我覺得像我這類誠實面對的人的聲音並沒有被外界注意到。現在社會上大概就三種聲音,一個是那些被指控造假的人的聲音,一個就是像蔡老師這類針對事情本質的評論聲音,還有第三種聲音,就是很酸,說你們做生醫的都是假的,發那麼多論文都是有問題的,拿了一堆錢,卻只出假貨。
我跟我的好朋友說,沒關係,我一定要努力,我要告訴人家不是臺灣做生醫的都是假的。我要好好的做,要告訴人家我們可以做得很好、也嚴謹。人都會有疏失的時候,但發生了疏失我會面對,我會盡我自己所有的力量,以證據去告訴人家說我這個地方已經澄清了。我要告訴人家,我們正正當當的做也可以投到頂尖的期刊,而且我不是為了追求高影響因子,而是要告訴人家我們臺灣的生醫學界對於世界上的生物醫學研究是可以做出真正的貢獻。
我是一個醫師科學家(M.D. Ph.D. Physician Scientist),我本來很滿意我自己的工作,覺得自己不只會做一般的臨床工作,也可以做基礎的生物醫學研究,而且做得還不會太差。但是現在M.D. Ph.D.卻變成一種恥辱,變成一種很丟臉的身分;我跟一位院士聊過,他說他也很沮喪,看到那幾個常見談論此事的網站,就覺得那個負面能量很強。今天做我喜歡的工作變成一件充滿負面能量的事,那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我經過非常久的沉思,最後還是決定積極面對,就是像我講的我盡所有可能用真實證據澄清。
再來要跟大家共勉打氣的是,在12月、1月事情鬧得最嚴重的時候,我還有論文在PubPeer上面的時候,我的2篇論文,一篇投到Nature Cell Biology,一篇投到Cancer Cell,剛好都是問題焦點的期刊,但我2篇論文都可以進入revise,而且Nature Cell Biology的編輯還請我審閱他們期刊的稿件。所以我相信,今天你個人如果處事審慎,有累積的口碑,雖然大環境的氛圍不佳,這個世界還是會給我們機會。我們就照著世界正常運作的規則走,就不會因為你的國家發生這些問題而被拋棄。
這些國際期刊給我論文的機會,對我來說是一個鼓勵,因為那是來自國際學術社群的聲音,不然若只看臺灣內部的評論,說實在的,我非常的沮喪。我覺得我的研究是真實的,那對我來說是靈魂的一部分,是我最努力看重的事情。今天不是說我本身被誣衊而已,而是整個臺灣陷於一種非常黑暗的狀況,做生醫研究的人變成是一種恥辱的身分。但我今天就要把這個恥辱化成一種力量,來告訴人家說,不是這樣,我們還是可以好好做,我們還是可以很謹慎的做,以前如果說有做錯的,我們會面對它,誠實的澄清、重複驗證,確定實驗的可再現性。我要用我的能力告訴世界,我們臺灣研究者的信用沒有變差,還是貢獻出第一流的東西給國際學術界。
今天我做這些努力,除了為我自己,一方面我也一直在想,我還能夠為臺灣的學術界多做什麼。後來我決定,就是往前走,要讓大家覺得,在這個事件之後的臺灣的生醫研究還是可以繼續做的。我們的研究不是不可以被質疑,被質疑了,就用證據澄清;不是不能有挫折,碰到了挫折,就去克服它。這段時間,我覺得我學到最多的是這個,當然這個代價很大,很痛苦,甚至動了放棄的念頭,但以真實的信念撐過了,就可以繼續走下去。
科:很高興聽到你今天談的這些,這是五個月來我覺得最有價值的一個訪問。
【訪談後閒聊】
科:你覺得投入基礎研究對您在臨床上的工作,有幫助嗎?
楊:有啊!我覺得我可以看到一些深層的東西,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臨床跟基礎這兩者是相輔的,病人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子的病癥,背後一定有些原因在那邊,這個原因得要走基礎研究才會知道;而做基礎研究的時候,我不會只去探討A分子或B分子的機轉,我都會去問一個臨床問題,譬如說這個病人為什麼對化療的反應不好、為什麼會轉移到淋巴、為什麼有的腫瘤會爛掉,那這種東西必須是邊看病人才會邊有想法的問題。
之前有一段時間我對於做研究實在非常有興趣,有點想說乾脆就只做研究。其實看病蠻辛苦的,有責任,既然喜歡做研究就不要當醫生,全職做研究或說看病當成副業就好。但是後來又覺得說,其實我的技術或是基礎研究的功力未必比其他研究者好,但是我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在於是我對臨床病徵的洞察力,我問的問題是臨床的問題,然後用基礎研究的方法去回答,這樣的結合,才比較容易產生對病人有利的研究。
科:這次事件衍生出一個額外的議題,到底醫師有沒有時間做研究?就您自己的經驗,醫師的評鑑升等要看什麼才合理?
楊:像臺大、榮總,這種一級教學醫院必須要做研究,這沒辦法,因為這是它的義務,他們如果不做研究那臺灣誰做醫學研究。那至於要不看論文,我是覺得說可以跟人家合作,醫師可以不用像我這樣自己整個統包,畢竟不是每個人的志向都是這樣,但他可以跟別人合作,譬如說,如果是一個純化學的論文讓一個完全無關的醫師來掛名,那就可能真的只是掛名,沒意義;但若是一位眼科醫師,他與其他人合作去創造了一種新的材質來替換眼角膜,雖然他不是材料科學家,也沒有去做那些材質的合成,但這個材料應用的發想跟最後在臨床上的試驗,沒有他就不行,那我就覺得這可以算是他的貢獻。當然,評審的委員是否有一致這樣的認知,也是很重要的,升等的評審委員們如果能以這樣的視野來看待,其實臨床醫師是否在研究上有貢獻,應該還是蠻容易就可以判斷的。
科:你會親自做實驗嗎?
楊:現在比較不會,因為雜事較多,以前剛有實驗室的時候,我是把自己當作是半個實驗人力。那現在不行,除了雜事太多,回家後得等到小孩睡覺後才能繼續在電腦前工作。禮拜六的時候,腫瘤科的醫生還要看病人,所以禮拜六上午看過病人後,我會跟學生相約討論,因為平常忙到沒時間跟他們討論,會待到下午,日常大概差不多都是這樣子。
科:好,謝謝,該問都問了,你也都誠實以告,我想大家都要重拾信心,開始過新生活了。
【附註:佐證資料】
【受訪者來函照登 】
楊慕華老師於4月17日來函更正說明:教育部曾去函陽明大學教務處詢問楊慕華老師受質疑的論文狀況,但人事室並無接獲相關訊息,亦無與楊老師接觸。台大則是以電郵詢問楊老師一篇共同作者論文的貢獻度,並無去文陽明大學,特此澄清。
本文由蔡孟利(《科學月刊》、《科技報導》總編輯)、李依庭(《科學月刊》、《科技報導》編輯)執筆,科學月刊授權使用,謹此致謝。原文出處
創建於1970年的《科學月刊》,當年一群留美的台灣學生,以「引介新知、啟發民智」興辦,是台灣最老牌的科普雜誌,內容涵蓋數學、物理、化學、生命科學、地球科學、環境科學、工程科學。
訂閱 《科學月刊》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